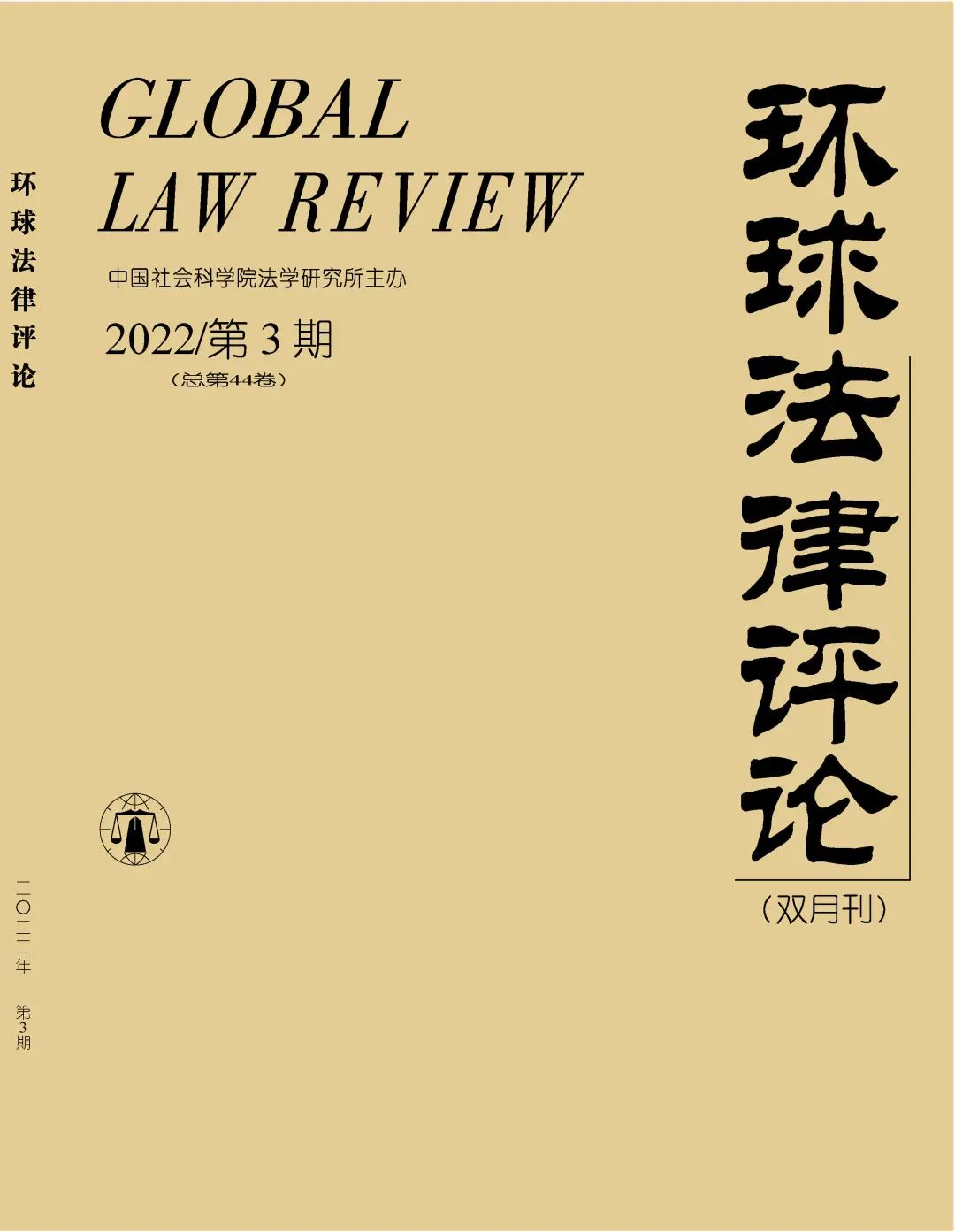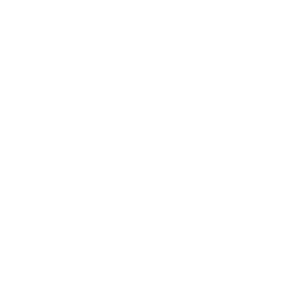杨金彪: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构成要素比较分析
点击上方蓝字 关注我们 如需转载本文,请在文末留言 杨金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构成要素比较分析》一文的正文,注释从略,全文发表于《环球法律评论》2022年第3期,原文请参见环球法律评论网站:http://www.globallawreview.org,或点击文末左下角“阅读原文”。 内容提要: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保护法益是复合法益,既保护女童性的自决权,也保护被害女童性的健康发展和正常性心理的养成。教育和医疗等机构的正常运转及公众信赖、性伦理等社会法益不是本罪的保护法益。本罪犯罪主体是负有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职责的人员。教育培训等机构的教师、一次性治疗的医生以及事实上的看护人员均属于本罪的主体。本罪在客观上要求发生了事实上的性行为,并不要求利用影响力或支配性,只要具备负有照护职责的身份就足以形成鼓励性。缺乏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以及被害人是否同意,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此外,本罪存在不作为犯及共同犯罪。本罪在主观上要求是故意,在发生认识错误的场合,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具体判断。特殊职责人员性侵女童的,要么构成与强奸罪的想象竞合犯,要么单独构成本罪。 关键词:照护职责 性侵犯 未成年被害人 复合法益 强奸罪 随着利用照护责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增多,许多国家的刑事法都相继做出回应。比如,德国刑法通过二十多年的修改,特别是2015年对相关条款的修改,形成以受保护人性侵罪为基础的一系列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日本刑法也于2017年分别增设监护人猥亵罪和监护人性交等罪。我国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下称“《意见》”)第21条第2款规定:“对已满十四周岁的女童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利用其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范,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以强奸罪定罪处罚。”2020年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下称“《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规定:“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女童负有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该女童发生性关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有前款行为,同时又构成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之罪的,依照 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增设提出了以下问题,在与强奸罪的比较上,本罪的犯罪构成具有什么特别之处,本罪与强奸罪之间的关系以及与非罪领域的界限等问题,以下从与德日刑法比较的视角进行考察。 一、本罪的保护法益之争 (一)学说分歧 关于本罪的保护法益,我国有单一说和复合说之争。单一说大致包括:女童性自主权说,青少年免受侵扰的性健全发展权说,身心健康说。复合说主要有两种观点:性自主决定权和身心健康权说,性的自决权和伦理禁忌说。在日本,其单一说认为,监护人与被监护人性交罪与强制性交等罪一样,侵害了不满18岁未成年人性自由、性自决权。因为行为人利用了不满 18岁未成年人对其在生活上、精神上、经济上的依赖关系,未成年人的同意不是依据自由意思决定做出的,因此本罪与准强奸罪具有同样的旨意,只不过射程范围更广。还有学者认为本罪的保护法益是性自由及性自决权,并从而否认青少年的健全育成是直接保护法益。复合说认为本罪的保护法益除了被害人性的自决权外,还包括儿童性的发育和健康养成。德国刑法学一般认为,本罪旨在保障儿童和青少年在某些依赖关系中的性自决和不受干扰的性发展。 (二)本罪保护的法益为复合法益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是对性侵犯罪的扩张,首要保护女童的性自决权。对于强奸罪的保护法益,尽管国外也有对性自决权提出质疑的动向,但是该说仍是通说。在我国,性自决权说也是强有力的学说。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并非对性同意年龄的提升。不承认女童具有性自决权会导致不协调,因为在非特殊职责人员与女童实施性行为的场合又不得不承认性的自决权。而在日本,一般都承认被害人性的自决(权)是保护法益。同时,本文认为,不能将本罪的保护法益概括为女童的身心健康。对于奸淫幼女的保护法益,多数说认为是幼女的身心健康。但是,身心健康是个过于宽泛的概念,指称并不明确。即使非要概括为身心健康,也必须限定为性的健康和正常性心理的养成。 因此,本罪保护的另一个法益是女童的性健康和性心理。首先,负有照护职责人员的性侵行为不仅侵犯了女童性自决权,还侵犯了其未来的性健康发展和正常性心理的养成。其次,保障女童性的健康发展和正常性心理养成是负有照护职责人员应尽的义务。女童性发育、性心理尚不健全,无疑需要负有照护职责人员进行正确的引导。最后,女童性的健康发展和正常性心理的养成具有补强不法程度的性质。日本学者认为,不满18岁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利用其影响力对被看护人形成压制状态,在罪质上可以评价为与强制性交罪同等。也有学者认为,在监护人对不满18岁的人继续反复实施性交行为的案件中,从时间、场所等特定性行为的情景看,不能判断存在暴力、胁迫,也不符合不能抗拒情况的,作为性犯罪追诉存在困难。因此,单纯从被害女童性自决方面寻找处罚根据,不足以揭示其犯罪本质,需要从行为人侵犯了对被害女童性健康发展和正常性心理养成所承担的义务上寻找根据。 综上,性健康发展说试图巧妙地避开对女童性自决保护而可能导致实质上限制其性自决权(积极自由)的指摘。还可能引发性自决权法益与性健康发展和性心理养成法益之间关系问题的思考,即这两种法益之间是否具有包容、替代关系的问题。性健康发展和正常性心理养成更多地是指向未来的发展权,性自决权则是指当下对性行为的支配权,因此,有必要从这两个方面理解本罪的保护法益。关于两种法益之间的顺序,日本有学者认为,对照监护人性交等罪的立法经过、宗旨以及构成要件,本罪有对被害人性自决权保护的一面,同时被害人身心健全的培养也是保护法益。相反观点认为,本罪的保护法益主要是儿童性的发育和性健康的养成,附带地也考虑儿童性自决。本文持前者观点,主张性自决权决定本罪的法益侵害性,性的健康发展和正常性心理的养成则具有补强法益侵害程度的性质。 (三)本罪保护法益的除外内容 其一,教育、医疗等机构的正常运转及公众对其安全秩序的信赖并非本罪的保护法益。在德国刑法中,规定有利用公务地位以及利用咨询、医疗或照护等关系的性侵害罪,学说认为此种情况性侵犯罪的保护法益还包括机构的无障碍运行及公众对其完整性的信任,这是基于规范的一般预防价值的考量。在我国,尽管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行为也有可能发生在教育、医疗机构中,但是,不能认为这些机构的工作秩序及公众对其安全秩序的信赖等超个人法益也是本罪的保护法益。首先,德国刑法关于发生在拘押机构、安置机构以及医疗机构内的看护人对被照顾女童的性侵行为是否构成本罪,以被害人与机构的高度依赖关系为基础。对于被委托从事教育、培训等人员与被害人发生性行为的情形,并不符合具有照护义务这个条件。我国关于本罪的构成客体具有同样的构造,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是对其所肩负的照护义务的背离,而非取决于女童对机构的依赖性。其次,性自决、性的健康发展和正常性心理的养成与机构的正常运转以及公众对其安全秩序的信赖是表里的关系。在机构内如果发生对受照顾女童的性侵犯行为,必然包含对机构的正常运转造成破坏并减损公众的信赖,但这种损害并不能揭示该罪的本质特征,不能看作是本罪的保护法益。最后,与强奸罪一样,本罪的保护法益是个人法益而非超个人法益。普通强奸罪也有发生在机构内部利用职务关系实施犯罪的可能,而强奸罪 并没有把机构的正常运转以及公众的信赖作为保护法益。因此,要求本罪同时保护超个人法益也是不合理的。 其二,近亲相奸等性伦理也并非本罪的保护法益。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属于自然犯,通常具有违背乱伦禁忌、恋童禁忌的性质,但是不能由此认为乱伦禁忌、恋童禁忌的性伦理也是保护法益。首先,本罪规定在强奸罪之后,保护法益与强奸罪相同,应当属于个人法益,因此,没必要将性伦理作为本罪的保护法益。其次,我国不像德国刑法那样规定了血亲性交罪。德国刑法血亲性交罪规定在调整身份关系、婚姻与家庭关系部分,保护法益是家庭秩序和性伦理。而其关于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则安排在妨害性自主犯罪的部分。显然,在德国刑法中,这两种犯罪保护的法益是不同的。我国刑法将本罪安排在强奸罪之后,可见考虑的保护法益在于被害女童的性自主和性健康,而非乱伦禁忌等性道德。最后,认为性道德是本罪的保护法益难以为女童的不可罚性提供根据。德国刑法第173条血亲性交罪规定,与直系血亲卑亲属性交的、与直系血亲尊亲属为性交的以及具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姊妹彼此间为性交的构成犯罪。尽管第三项规定,行为时不满18岁的,则该直系血亲卑亲属与兄弟姊妹不处罚,但是,仍难以否定其行为具有不法性。如果认为本罪的保护法益包括乱伦禁忌等性道德,就难以否定女童行为的不法性。即使女童因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侥幸逃脱刑事处罚,但仍然可能因为刑法第17条第4款的规定遭受不利益。从本罪意在保护被害女童性自主及性健康视角,即便在被害女童的贡献超过了必要共犯的限度场合,也不具有可罚性。 二、负有照护职责人员的射程 在日本,监护人性交等罪的犯罪主体范围相当狭窄,属于身份犯,仅限于监护人。德国刑法关于本罪的主体范围则非常广泛,但要求犯罪主体与被害人之间必须存在某种特别的关系,也属于身份犯。我国刑法把本罪的主体范围设定为,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女童负有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这里的“等”一般认为还包括其他的特殊职责人员,例如狱警等监管机关的工作人员;负有解救被拐卖妇女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等。因此,本罪犯罪主体的范围并不能拘泥于文义,应当综合考量予以确定。尽管本质上起决定作用的是行为人是否对被害人负有照护职责,即行为人是否与女童共同居住,是否照料其日常生活、负担生活费支出等经济状况,以及负责其教育、医疗事项,实质是能否对女童的决断包括性自决做出准确判断产生影响,行为人是否负有保护女童性的健康发展和正常性心理养成的义务。 (一)监护人、收养人 监护人、收养人是指我国《民法典》总则编规定的监护人以及婚姻家庭编规定的收养人。在日本,监护人性交等罪要求犯罪主体必须是事实上的监护人,即日本民法第820条所规定的处于实质上对未成年人监督以及保护立场的人。事实上的监护人判断标准的立法解释,是指不问有无法律上的监护权,只要事实上持续地负责未成年人的生活,包括经济上的供养以及指导监督等精神上的培育,存在依赖与被依赖、保护与被保护关系的人。因此,即使是有法律上监护权的人,如果不存在事实上的监护与被监护的状态,也不是事实上的监护人。即使不具有法律上的监护权,但事实上却对未成年人具有监督、保护责任的人,也符合“事实上监护人”的要求。我国对监护人的理解也应当考虑事实上负有监护职责的情形,因此,尽管负有首要监护职责的父母仍然在世,但如果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与子女共同生活,那么,与未成年人形成监护关系的祖辈或兄姐可以视为事实上的监护人。收养关系属于拟制血亲关系,收养人的认定与血亲关系认定等同。 (二)负有教育、医疗职责人员 负有教育、医疗职责的人员主要是指在相应的教育机构对女童负有教育职责的人员。前提是行为人在教育机构中负有教学和管理等职责。被害人在该机构中接受教育。也有论者主张教育机构中的管理人员不属于本罪主体。日本法中本罪的主体仅限于监护人,不包括教育、医疗等机构人员。其理由是,对于教师、体育教练等,不能认定涉及全部生活的依赖被依赖、保护被保护的关系。我国刑法考虑包括这些人员在于负有教育、医疗职责人员对女童发展所具有的某种权威性,应当综合考虑培训场所、培训次数、培训方式、培训人数等因素判断上述人员的职责是否能够对女童性自决产生影响,上述人员是否负有保护女童性的健康发展和正常性心理养成的义务。教育机构中不负有教学和管理职责的园艺师、公寓的管理者、清洁工等对女童不存在这种权威性,因此不在该犯罪主体之列。同样,负有医疗职责的人员对女童病患也存在这种权威性。当然,这里的负有医疗职责的人员并不限于取得医师资格的人,也包括江湖郎中等非法行医者。因为不处罚非法行医者的性侵行为将会导致不公平,产生处罚的漏洞,也不符合刑事政策的目的。存在争议的是对于临时的、一次性的医疗关系的场合是否构成本罪。否定说认为,应从实质规则即“对于青少年的育成发展具有实质性的管护作用”进行判断,认为加害方与被害方短期、偶然的接洽难以形成对被害人的支配关系。实质判断的方法无可厚非,值得讨论的是特殊职责地位是需要达到支配的程度,还是只需要对女童性自决的准确判断具有重大影响就可以。在医疗关系中,患者由于缺乏相关专门知识,对医疗工作人员具有高度依赖性,处于极度不平衡的关系下,并对医疗工作人员高度信赖,因此即使一次性的医疗关系,也可能存在导致女童对性自决难以准确判断的情况。而且,鉴于医疗工作者特殊的职业义务,认定其对作为病患的女童性健康发展和正常性心理养成负有保护义务不存在太大障碍。因此,在一次性医疗关系的场合,足以形成性支配关系,所以不能排除一次性医疗工作者成为本罪主体。 (三)负有看护职责的人员 负有看护职责的人员主要是指在依法成立的机构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未成年救助保护科(室)的救助管理站等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中,对女童负有看护职责的人员。基于合同关系对女童负有看护职责的人员,例如看护女童的保姆以及父母临时委托邻居看护女童的场合等。被委托看护女童的保姆和邻居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因为,从文义理解上难以径直得出要求具有长期职责关系的结论。同时,被委托暂时看护女童的邻居,除了看护时间短之外,如果其负责女童的生活起居,就难以否定这种看护关系可能对女童构成某种支配性,包括性自决的支配性。另外,在法律上不属于监护、收养关系的负有看护职责的人员,例如《民法典》第1107条规定孤儿或者生父母无力抚养的子女,可以由生父母的亲属、朋友抚养,这里的亲属、朋友也属于负有看护职责的人员。因自愿接受等行为而具有看护职责的人也应当包括在内。此外,负有看护职责人员还包括基于某种事实的看护人,例如,德国刑法第174条规定的行为人可以是对同居伴侣的未成年后代实施性行为的人,将刑事责任扩展到同居关系中。德国学者认为构成犯罪的前提是行为人同与被害人相关的人员之间存在同居关系。至于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是否存在家庭关系,甚至是否需要有任何形式的社会接触都在所不论。但是,我国学者则认为,只有在行为人与同居性伴侣的直系卑亲属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家庭关系,才具有使被害人对性自决难以作出准确判断的可能,所以,是否形成事实上的看护关系才是重点,包括在祖辈尊亲、兄等近亲属对女童实施性侵的场合。因此,即使不存在家庭关系,如果事实上与被害人具有生活上依赖关系的所谓“干爹”“养父”,也可能构成本罪主体。总体上看,负有看护职责的人员可以视为一种兜底性规定,凡是不属于负有监护、收养、教育、医疗关系的,但基于法律规定、合同关系、自愿接受行为等的看护职责以及其他事实上具有看护职责的都属于这里的看护关系。而且,看护职责与其他职责之间可能并不具有严格的界限。例如,按照《儿童福利机构管理办法》的规定,儿童福利机构主要收留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未满18周岁儿童,儿童福利机构中的工作人员既可以认为是代替儿童福利机构履行监护职责的人,也可以认为是负有看护职责的人。 看护人中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主体,就是接收离家出走儿童的接收人。对接收人的身份认定问题,在日本,是否承认离家出走儿童接收人的“事实上监护人”身份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此类接收人因为没有出走儿童方面的委托,不是监护人身份。亲子关系是本罪从属关系的基础,接收人与出走儿童之间不存在拟制的亲子关系,因此接收人原则上不是保护人。但是,在我国,离家出走儿童的接收人可以构成本罪。一是日本刑法监护人性交等罪法定刑较高,与强奸等罪的不法性难以相当,所以学说倾向于限制解释。德国对于受保护人的性侵罪设置了低于强奸罪的法定刑,不存在限定解释的契机。所以学者们认为离家出走的未成年人也可以委托给实际接管人照管。我国负有照护职责性侵罪也设置了低于强奸罪的法定刑,没有限定解释的必要。二是日本刑法的犯罪主体限于监护人,文理解释的空间有限。德国的犯罪主体范围广,将接收人纳入本罪主体没有障碍。我国的犯罪主体范围也非常广泛,特别是负有看护职责人员的规定,可以涵摄离家出走儿童的接收人。三是日本刑法监护人照护义务来源于民法典明文规定,其解释受到民法典规定的严格限制。我国刑法的义务来源非常广泛,特别是在负有看护职责人员的场合,甚至包括了基于生活事实而形成看护关系的情况。在离家出走者的场合,就是基于自愿接受行为引起的照护义务。尽管离家出走者的接收人并未受到离家出走者父母的委托,但是,在离家出走者暂时脱离了父母保护的场合,高度地依赖于接收人的保护。依据自愿接受的法理,自接收人的行为阻断离家出走者父母及其他人现实上行使照护义务的那一刻起,应当负有对离家出走者性自决、性健康的发展和正常性心理养成的保护义务。四是离家出走者往往对于接收人在生活和精神上形成事实上的依赖关系,因此,在接收人与之发生性关系时,离家出走者难以对性自决作出准确判断。 (四)主体身份不明朗 对于监护人与女童存在恋爱关系的情形,日本学者首先从保护女童性发展以及健全的性心理培育立场出发,认为监护人具有保护和教育儿童对监护人所具有的情感不转化为性感情、性关系的义务,否则,仍然有构成本罪的可能性。哪怕是在监护人继续地滥用监护身份而导致被害人价值观发生重大变化,积极实施性交行为的场合。特别是,如果这种恋爱关系的形成是在行为人成为特殊职责人员之后而产生的,则难以排除不法。当然,不排除在行为人成为特殊职责人员之前,双方已经具有爱恋关系的,特殊职责人员不构成本罪。 三、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行为的 (一)发生了事实上的性行为 本罪的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与女童发生性关系。表现在:一是这种性关系仅限狭义的性交,不包括单纯的猥亵行为。二是包括女童主动的场合也构成本罪。德国刑法学认为,任由实施性行为不单纯是不作为,“特殊职责”身份已经具备了某种确实的鼓励性。但是我国刑法没有要求确实的鼓励性。三是构成本罪不需要以暴力、胁迫作为手段,也不需要乘人之危。这一点与奸淫幼女之外的强奸罪不同。四是本罪的既遂以插入说为标准。五是本罪是行为犯。将本罪界定为危险犯的理解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我国刑法传统理论。六是本罪行为并不需要持续性。 (二)是否利用影响力或支配性 行为人具有特殊职责就意味着对被害女童形成事实上的影响和支配性,因此,负有照护职责可以看作是本罪行为人的主体特征,也即本罪构成主体是一类特殊主体。但在本罪构成行为上是否利用了这种影响力或支配性是存在争议的。比如,在日本,构成监护人性侵等罪要求必须利用事实上是监护人所产生的影响力。表现为利用了被害人对父母等监护权人的要求难以拒绝的心理状况而达到性交的目的。包括因为与监护人的性关系继续地常态化被害人感情处于麻痹的情况,以及存在强制、强要、意思压制的程度比较轻微的情况。德国刑法则要求有滥用以及与教育、培训等关系相结合的依赖性。构成滥用的先决条件是,在犯罪时具体存在事实和/或心理的依赖,而且双方都知道这一点。 我国刑法只要求行为人具有特殊职责,一般情况下双方都认识到这种地位而发生性关系就可以。首先,条文文本并没有要求利用特殊职责,也没有要求利用具有特殊职责的影响力。其次,本罪显然扩大了处罚范围,如果仍然要求行为人利用特殊职责或者特殊职责的地位迫使女童就范,就完全没有增设的必要。最后,如果要求利用影响力则有可能无法实现保护被害女童的目的。对此,国外立法和学术解释都存在争议,比如,日本刑法明文要求“乘具有影响力之机”,但学者多数则认为并不要求积极利用影响力的行为(诱惑、胁迫等),因为,“监护人的身份”本身就满足了“乘具有影响力之机”的要件。对此,我国刑法没有作出严格限制的必要,因为对于已满14不满16周岁女童,监护等特殊职责足以形成一定的影响力。 (三)未成年被害人同意无效 尽管日本学界对被害人同意是否构成监护人性交等罪存在不同看法,但是多数学者认为,即使被监护人承诺了性的行为,因为承诺本身是在监护人的影响力之下形成的,不能由此否定监护人性交等罪的成立。甚至在行为人误信被害人同意实施性交等情形时,对本罪的故意也没有影响。我国刑法学者也认为,在奸淫幼女罪中幼女的同意无效,本罪应作同样理解。即刑法对这类女性采纳了家父主义的保护原则。首先,特殊职责人员与女童发生性行为,正是利用了女童在行为人特殊职责影响下难以对自己的性自决做出准确判断的情况。其次,本罪的保护对象仅限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低于日本刑法或德国刑法的18岁,很难承认该年龄段的人在特定人际关系下能够准确做出同意的意思表示。最后,特殊职责人员负有保障女童性的健康发展和正常性心理养成的义务,不受女童同意与否的影响。 (四)本罪的不作为犯和共犯问题 如果第三人有义务对本罪行为进行干预而不作为可以构成不作为的帮助犯。例如校长明知某教师对学生有性侵行为而未采取措施阻止并放任不管的。日本刑法和德国刑法都认为本罪的成立以实施性行为的身体接触为前提,因此得出本罪是亲手犯的结论。然而,根据我国刑法理论,该罪不属于亲手犯,不排除构成共同犯罪的可能。例如,父亲让自己15周岁的女儿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首先,从文义上看,尽管条文描述为“与该女童发生性关系的”,并不意味着亲自发生性关系。正如强奸罪描述为“强奸妇女的”,但是强奸罪并非亲手犯。其次,不能由本罪是身份犯或者义务犯就径直得出不构成间接正犯的结论。是否可以构成间接正犯应当进行实质判断。本罪的实质在于,行为人对女童具有特殊职责,使女童对性自决难以作出准确判断。特殊职责人员将女童交由第三人发生性关系,特殊职责人员的影响力没有变化。而且,也背离了其对女童性的健康发展和正常性心理养成的保护义务,因为这种义务不仅包括亲子关系不能转化为性关系的义务,还包括阻止他人利用自己地位的义务。最后,日本也有学者认为监护人性交等罪在没有身份的人参与的场合,根据参与形态,成立本罪的共同正犯、教唆犯、帮助犯。这就并没有完全排除特殊职责的人可以构成间接正犯。那么,第三人是否应受处罚?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因为第三人作为帮助犯,其行为通过利用特殊职责人员的特殊地位违背了培育女童性自决、性的健康发展和正常性心理养成的义务。不过应当以第三人认识到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特殊职责关系为前提。 四、本罪主观上要求存在故意 在教义学上,几乎没有争议地认为本罪在主观上存在犯罪故意,即与已满14不满16周岁被照护女童故意发生性关系的行为。这可能会发生认识错误的情形,在行为人认识错误的场合,可能影响是否构成本罪故意的认定,从而影响是否成立本罪。 首先,对象的认识错误。如果行为人将自己负有照护职责的人误认为其他人而对之实施性侵犯的,由于不构成本罪的故意,因此不能构成本罪。 其次,对被害女童年龄的认识错误。必须主观认识和客观事实相一致时才能确定为本罪。比如,行为人误以为被害人年龄超过16岁而实施性侵的,就不能构成本罪。那种基于推定“应当知道”可以构成本罪的观点不妥。 最后,对于自己所承担特殊职责的性质认识错误,或者对于自己所在机构的性质认识错误,属于涵摄错误,通常不影响犯罪故意的成立。例如,行为人因为自己的行为并不符合收养的形式条件误以为自己不是负有收养职责的人员;对自己是否属于看护人员产生错误认识的,或者教育矫正机构的教育工作人员误以为自己所从事的并不属于刑法第236条之一的教育职责的,都不影响本罪故意的成立。 五、本罪与强奸罪之间的关系 在教义学上有必要将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与强奸罪进行比较,以便更深入地理解本罪。刑法第 236条之一规定了两罪的基本关系,即规定“有前款行为,同时又构成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也就是本罪行为可能会构成两罪,产生竞合问题,因此采取择一重处罚的原则。但是对该条款的性质在学理上还存在不同认识。有学者认为,本条是对强奸罪的补充条款,因此本罪与强奸罪之间构成补充关系的法条竞合犯。也有论者认为,本罪的保护法益还包括被害人性的健康发展和正常性心理的养成,与强奸罪之间应当是想象竞合的关系。从法条表述上看,本罪的构成并不要求暴力等手段,因此,在行为人采取暴力、欺骗等手段性侵被照护人的,就会发生与强奸罪的区分问题。 (一)通过暴力、胁迫手段 根据日本学者的观点,在不满18岁的人由于暴行、胁迫而被迫与监护人性交的场合,不满足“乘具有影响力之机”的要件,成立强奸罪。但是本文认为,因特殊职责人员使用暴力、胁迫手段,就断言妨碍到特殊职责的身份、地位的影响力缺乏说服力。同时,即 便采取暴力等行为也改变不了行为人违背了保护女童性健康发展和正常性心理养成义务的一面,因此,这种情况应当成立强奸罪与本罪的想象竞合犯。 但是,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本罪只是处罚强势关系下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的犯罪。只要暴力未达到使女童显著难以反抗的程度,就只能成立本罪。这就可能与“胁迫”发生混淆。在通过胁迫手段实施性交行为的场合可能存在区分上的困难。在日本,利用地位、关系等优势如果行为手段符合胁迫的,也可以适用强奸罪。对于强奸罪上所谓的暴行、胁迫的概念,判例认为“只要达到使对方的抗拒显著困难程度就够了”。在具体的判断上,即使根据列出的暴行、胁迫行为判断,认为没有达到暴力等程度,但是“伴随着对方的年龄、性别、品行、经历等,实施行为的时间、场所的周围环境以及其他具体情况,使对方不能抗拒或者陷入困难就够了”。日本刑法第 178条规定了准强制性交等罪,是以乘“心神丧失”或者“不能抗拒”之机,或者使他人进入这种状态而达到性交的场合为对象。在学说上也有通过扩大解释,将高尔夫教练、牧师、俱乐部顾问等,利用对未成年人构成的优势地位、关系,使被害人陷入恐怖、惊愕的场合,使其害怕遭受不利益而答应性行为的场合,认定为不能抗拒的观点。在我国,如果特殊职责人员单纯利用职责影响力,实施的行为达到使被害人显著难以反抗的程度时,不排除构成强奸罪的可能性。例如,父母、养父母等长时间不给食物吃、不给衣服穿,或者以此为要挟,如果使被害人显著难以反抗的,构成强奸罪与本罪之间的想象竞合犯。因此,在刑法增设了本罪之后,《意见》第21条第2款关于“以强奸罪定罪处罚”的规定依然有效。 (二)通过欺骗实施性交场合 德日刑法在构成特殊职责人员性侵罪上都强调了满足“乘具有影响力之机”的要件,例如,在监护人于黑暗中或者化妆间实施奸淫的场合,就不符合“乘具有影响力之机”。本文认为,在特殊职责人员隐瞒自己身份实施骗奸的场合,譬如某中学老师甲,通过假扮成乙与已满14周岁的女学生丙发生性关系,如果丙知道是自己的老师甲就不会与其发生性关系,因为违背了女童与谁发生性关系的性自决,由于欺骗使其不法侵害程度高于本罪,应当以强奸罪定罪处罚。但如果丙知道甲是自己老师就会同意的场合,应当认定甲的行为构成本罪。首先,甲作为对丙的性自决、性健康发展和正常性心理的养成负有照护职责的人员,故意予以侵犯,客观上具有侵犯女童性自决、性健康发展和正常性心理养成的不法性。其次,不承认上述情况构成本罪,将形成处罚的漏洞,也不符合刑事政策的要求。最后,与德日刑法相比,我国刑法更注重身份的有无。德日刑法不仅要求有身份,还要求“乘具有监护人影响力之机”或利用依赖关系。 此外,如果行为人欺骗被害人误解其行为性质的,构成强奸罪。例如在弗莱特瑞(Flattery)案中,被告人谎称对被害人实施外科手术而实际上实施了性交行为,被判决构成强奸罪。这种情况成立与本罪的想象竞合犯,择一重处。有疑问的是,在行为人使被害人误以为性行为是治疗的必要手段而实施奸淫的,是否构成强奸罪。在英美法上,医生通过虚假宣称可以治病而诱使生病妇女与之性交,不构成普通法强奸,因为普通法认为诱因中的欺诈不会使同意无效。然而,尽管被害人对实施性交行为有误解,但性行为具有繁衍后代的社会属性和两性愉悦的自然属性,行为人妄称性行为是基于治疗的目的,而且使女童对此深信不疑,显然是对性行为目的的隐瞒欺骗,导致被害人本来就不能实现的性行为目的落空,因此应当构成强奸罪。在特殊职责人员实施的情况下,同时构成与本罪的想象竞合犯。 六、余论 尽管《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增设强化了对未成年人性犯罪的刑法规制,但是囿于我国刑法的立法传统和固有体系,性犯罪的刑事立法依然显得过于保守。第一,本罪的侵害对象仅限于已满14不满16周岁的人,处罚面过窄。性自决的能力是对与性有关事项的判断能力,未成年人往往不具有足够的判断能力。很多国家的犯罪对象都是不 18岁的人,不仅德国、日本如此,英国《2003年性犯罪法》(Sexual Offences Act 2003)同样考虑不满18岁的人可能不能进行成熟的判断而产生性虐待、性剥削(即产生保护的必要性),最终把犯罪对象确定为不满18岁的人。否定未成年人在特定条件下具备性自决的判断能力与是否肯定其具有性自决权不是一回事。将不满18周岁的人纳入性犯罪的保护年龄,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性自决权,而不是为了限定未成年人的性自决,所以学界考虑未满 18周岁的人是否应该具有性自决权,或者担心将本罪的行为对象设置为不满 18周岁的人涉嫌侵犯其性自决,既不合理也不具有说服力。第二,刑法只是规定了奸淫的行为,而现实中还存在很多猥亵行为得不到处罚。第三,只保护女童而不保护男童,造成性别的差别对待也是不恰当的。上述问题都不是解释论的问题,只能期待刑事立法的跟进。
转载时烦请注明转自“《环球法律评论》公众号”字样
——恋人关系的视角
成立要件
实施性侵犯场合两罪的界分
两罪的界限
- 上一条: 刑法教义学中的当然推理 2024-06-01
- 下一条: 朱光星:《刑法修正案(十一)》后我国的性同意年龄制度反思——以中国与欧洲之比较为视角 2024-06-01
- 刑法为何增设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 2022-12-10
- 刑法为何增设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 2022-10-30
- 张明楷: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15周岁的少女主动与男教师发生性行为,男教师成立本罪吗? 2022-11-09
-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二十七条【增设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 2022-09-06
- 张明楷:强奸罪Ⅱ——骗对方与自己发生性关系才能被录用,构成本罪吗? 2022-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