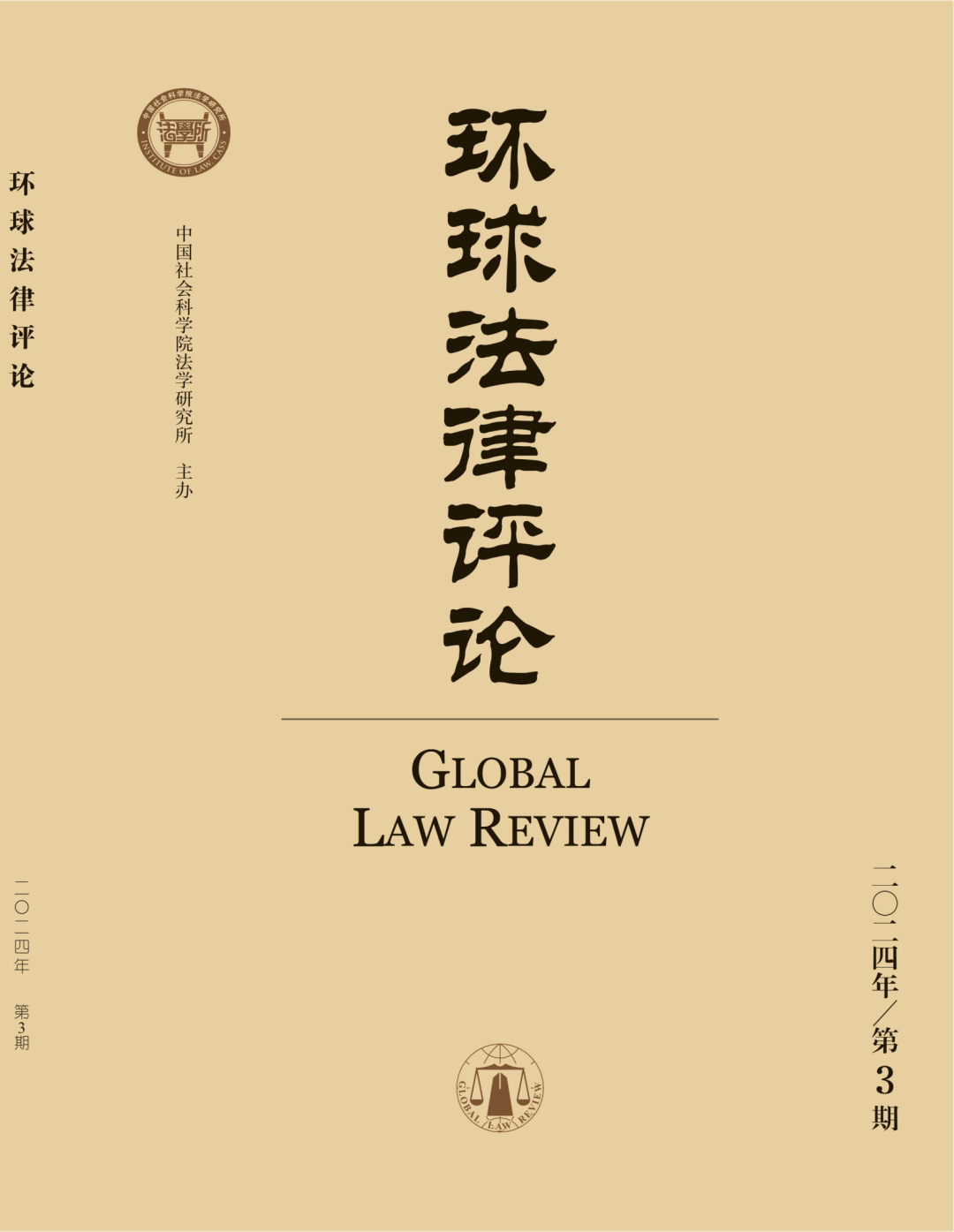原创 陈兴良 环球法律评论 2024-05-31 08:48 北京
如需转载本文,请在文末留言
转载时烦请注明转自“《环球法律评论》公众号”字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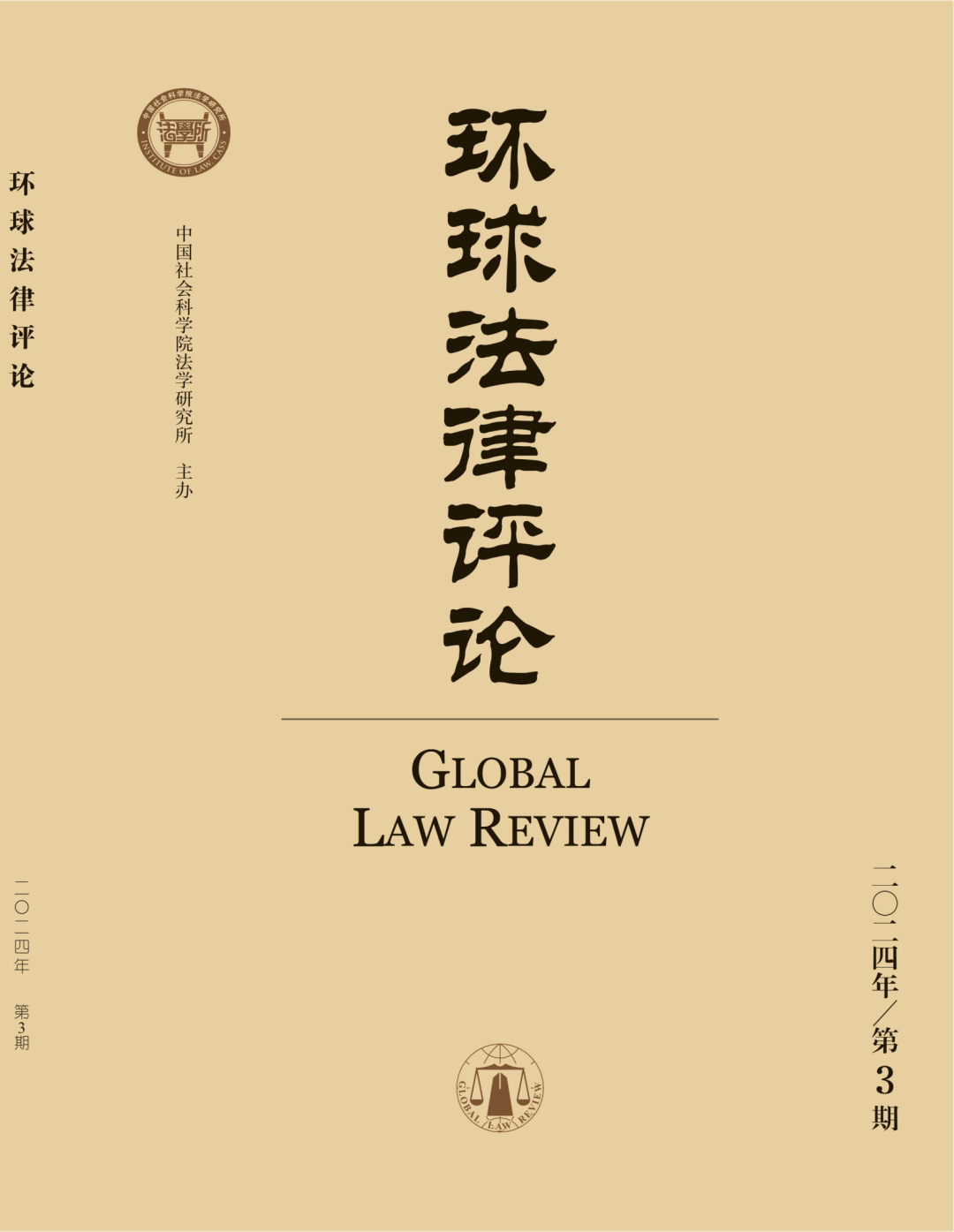
内容提要:当然推理是两个事物之间存在当然之理,因而可以将其中一个事物与另外一个事物同等对待。可以说,当然推理是以当然之理为根据的一种逻辑推理。当然推理之“当然”可以分为逻辑之当然和事理之当然,基于逻辑之当然的推理,因为两个法条规定的事项之间存在逻辑上的递进关系,并且后一事项被前一事项所涵盖,因而在刑法中适用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基于事理之当然的推理,则以小推大或者以大推小,虽然具有事理上的合理性,但它是以法无明文规定为前提的,因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适用中不得采用。
关键词:法律推理 当然推理 当然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
作者:陈兴良,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24年第3期
因篇幅较长,注释从略。
原文请参见环球法律评论网站:
http://www.globallawreview.org,或点击文末左下角“阅读原文”。
刑法的当然推理作为一种推理方法,相对于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而言,是一种鲜为人知的推理方法。在各种法律推理的著作中,甚至没有当然推理的一席之地,而是将其归之于法律解释方法。本文拟在对当然推理与当然解释进行辨正的基础上,对当然推理的性质与适用等问题加以论述。 如果从字面上解读,当然推理是指基于两个事项之间的当然之理所进行的法律推理。可以说,当然推理在所有法律推理方法中是最为陌生的,而且当然推理这个概念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表述。当然推理是从拉丁语argumentum a fortiori翻译过来的,其含义是基于更强论据所进行的论证,正契合于中文当然推理之义。 当然推理的性质是指基于当然之理所进行的论证究竟属于推理还是解释的问题,也即当然推理与当然解释的界分,这是在我国刑法方法论中争议较大的问题。在我国传统刑法解释学中,当然推理通常被称为当然解释,因此,对当然推理的概念界定不能不始于对当然解释和当然推理之间关系的梳理。 无论是当然推理还是当然解释,都是以两个事项之间存在当然之理为前提的。至于通过这种当然之理所进行的论证过程属于何种范畴,从德日法学方法论来看,日本称为解释,将当然解释与类推解释相提并论,归之于论理解释,以此区别于文理解释。德国则称为推理,例如德国学者指出:“‘举强以明弱’(argumentum a fortiori)也被称作当然推论。人们从某一特定法效果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推导出其与其他案件事实的关联。理由是后者的关联比前者更为紧密,即所谓‘既然……那么当然也……’。”在此,德国学者明确地将当然推理界定为是基于两个事项(法效果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系而推导出更为紧密的关联,因此符合推理的性质。 我国通说认为基于当然之理所进行的论证活动是解释,因而称为当然解释,我国也存在个别学说将当然解释称为当然推理。除此以外,我国还存在竞合说,认为基于当然之理所进行的论证活动具有解释与推理的双重属性,这种观点指出:“当然解释(其基础是当然推理)是指法律上虽无明文规定,但依规范目的衡量及逻辑上或事理之上的当然之理,将法律未明文规定的事项与已明文规定的事项进行比较,该事项比法律已明文规定之事项更有适用的理由而适用该法律规定的方法。”在以上概念中,我国学者将当然推理与当然解释视为一体,认可当然推理和当然解释这两个概念可以并行不悖。由于上述对当然解释或者当然推理的定义,我国学者明确认为是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前提的,因而将此种情形能否称为当然解释,首先涉及对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这两个概念的功能辨析。 法律解释是指对法律文本语义的阐释,以法律的明文规定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法律解释始于语义亦终于语义,始终存在于法律文本可能语义的空间。因此,法律解释具有语言分析的性质。德国学者指出:“所有进一步的解释努力都以可能语义为基础:它们总是在语言习惯所许可(可能还受到法律定义限制)的语义空间内进行。它们必须在这一空间内确定能够最恰当地赋予有关法律语词的语义。”当然解释揭示的当然之理并不是法律文本的应有之义,这也就否定了当然解释是一种解释方法。应当指出,在以往的论述中,我亦曾经基于当然解释的立场对其前提作了论述,认为在当然解释的情况下,刑法条文表面虽未明确规定,但实际上已包含于法条的语义之中。在此,存在语义与文本的分离,亦即认为语义可以脱离文本而存在,显然是与解释概念相悖离的,因而值得反思。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文本不存,则语义何所依附? 然而,问题在于如何判断是否法律有明文规定?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有规定是指法律有明文规定。当然,这里的明文规定不仅包括显性规定还包括隐性规定。显性规定是指字面规定,而隐性规定则是指虽无字面规定,但具有逻辑涵摄关系。例如,在走私黄金进口的案件中,虽然不符合走私贵重金属罪的构成要件,但却该当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构成要件,在此黄金被普通货物、物品所涵摄,因而通过解释就可以将黄金包含在普通货物、物品概念之中,对走私黄金进口的行为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论处并无疑问。然而,在事物之间存在逻辑上的递进关系的情况下,例如伤害与死亡,伤害为轻,死亡为重,经过伤害可以达致死亡。如果法律只对死亡作了规定,能否认为这一规定也适用于伤害呢?换言之,法律对死亡的规定是否包含了对伤害的规定?例如《唐律·名例》“断罪无正条”的疏议在解释《唐律·贼盗律》“夜无故入人家,主人登时杀者,无论”规定的时候指出:“假有折伤,灼然不坐。”那么,在《唐律》规定了“杀”的情况下,对于“伤”到底是有规定呢还是没有规定?对此,答案是没有规定。因为该事例正是对“断罪无正条”的解释。在此,已经明确法律对于“折伤”属于“无正条”,也就是没有明文规定。由此可见,可以从明文规定中通过逻辑推导出相关内容,并不等于相关内容包含在法律规定之中。因此,从“登时杀者,无论”的规定中引申出“折伤,灼然不坐”的结论,并非解释而是推理,也就是当然推理。 那么,为什么会把上述情形称为当然解释呢?本文认为,当然推理之所以被视同当然解释与我国刑法方法论中没有专门论述刑法推理相关。我国传统刑法方法论受到日本刑法解释学的影响,将刑法推理与刑法解释糅为一体。例如日本学者将文理解释与论理解释相提并论,明确地把类推解释称为论理解释。我国刑法教科书在论述刑法解释时,通常也将刑法解释分为文理解释和论理解释。文理解释是指对法律条文的字义,包括单词、概念、术语以及标点符号,从文理上所作的解释,是围绕语义所展开的解释活动。文理解释采用的是语言分析方法,这是刑法解释的主要方法。此外,相对于文理解释还有另外一种解释类型,这就是论理解释。论理解释是指按照立法精神,联系有关情况,对刑法条文从逻辑上所作的解释。因此,论理解释中的论理是指逻辑,在这个意义上说,论理解释是指采用逻辑分析对刑法进行解释的方法。 现在看来,这种将刑法解释分为文理解释和论理解释的分类显然存在一定问题。对刑法解释采取这种两分法的思路,虽然有利于从语言和逻辑这两个面向较为全面地把握刑法解释方法。但刑法解释是对刑法文本的解读,它是以法律有明文规定为前提的,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解释这一概念就难以成立。例如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指出:“解释总是基于某个给定的东西,即文本。”由此可见,法律解释是以法律文本为根据的,因而是以语言解释为中心而展开的,其他方法只是对语义解释的补充。此后,萨维尼将体系解释与逻辑解释糅合在了一起。另外,在利益法学和价值法学的影响下萨维尼又补充了目的解释,由此将法律解释形式最终归纳为四种方法,即语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又被称为四要素说,成为法教义学的通说。有德国学者曾经引用德国联邦法院对四种解释方法的以下表述:“服务于解释目标的有基于规范文义的解释(文法解释),基于自身关联性的解释(体系解释),基于规范目的的解释(目的解释)以及基于立法材料及立法史的解释(历史解释)。”应该说,法律解释方法的四分法以语义解释为中心,以体系解释、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为补充,形成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方法论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相分离:只有以法律文本为对象的阐释活动才能称为解释,除此以外可以归入法律推理的范畴。在我国传统刑法解释论中,扩张解释和限制解释可以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是未超越语义范围的扩张解释与限制解释,此时的衡量标准是通常语义。扩张解释是指对法律规定做超过通常语义的解释,限制解释是指对法律规定做小于通常语义的解释。无论是扩张还是限制,都没有超越语义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说,未超越语义范围的扩张解释与限制解释仍然属于语义解释的范畴,而不是论理解释。第二种是超越语义范围的目的性限缩和目的性扩张,目的性限缩是指小于语义范围的实质推理,目的性扩张是指大于语义范围的实质推理。因此,这种超越语义范围的目的性限缩与目的性扩张就不是语义解释,而应当归入具有漏洞填补功能的实质推理。通过以上对解释与推理的辨析可以确定,两者区分的主要根据就在于是否超越法律文本的语义范围。只有在语义范围之内,才存在法律解释的问题。超出法律文本的语义范围,则不可能是法律解释而应当归之于法律推理。因此,传统刑法解释论中的论理解释是不能成立的,应当将基于当然之理所进行的论证方法归之于法律推理。 法律推理是一种逻辑分析方法,它不同于作为一种语言分析方法的法律解释。我国学者曾经对论理解释定义如下:“论理解释是指不拘泥于法律条文的字面意思,而是斟酌法律理由,联系一切与之有关的因素,依一定的标准进行推理、论证来确定和阐明法律文本的解释方法。”本文认为,上述定义完全将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相混同。论者将类推解释和当然解释都归之于上述论理解释,但同时又认为它们是解释方法。不可否认,解释和推理确实在一定条件下是存在竞合的,即某种方法既是解释又是推理。例如在法律文本语义范围内,基于类比推理对法律所作的解释,作为解释方法是指同类解释,作为推理方法是指类比推理。因此,如果是在法律文本语义范围内采用推理方法进行解释的,就是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的竞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同时符合解释与推理的特征。然而,如果是在法律文本语义范围外进行推理的,就只能是单纯的法律推理而不可能是法律解释。因为超出语义范围就不存在解释,这是解释的基本特征。如果把类推看作是推理的典范,那么,德国学者的以下论述可以视为是对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之间界分的准确表述:“如果说解释所要做的仅仅是阐明法律规范或者法律概念的关键性意义,并且限制在对法律规范或者法律概念的意思解读之上;那么类推所寻求的则是离开法律文本来框定的直接适用范围。解释的目的是将法律意思明了化,使之在面对出现的相应情况时能够适应今天已经变化了的要求与观点。类推的目的相反则是通过扩展和进一步发展法律条文而填充法律的空白。”由此可见,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类推是将法律规定推导至与其具有最相类似关系的事项,并不能被法律规定所涵摄。在当然推理的情况下,如果是基于事理上之当然推理,则法律规定的事项和与之存在事理之当然关系的事项之间也不具有包含关系。因此,上述两种情形都是对法律规范的一种扩展适用。然而,在逻辑上的当然推理中,法律规定的事项虽然字面没有规定,但在逻辑上涵盖与之存在逻辑上之当然关系的事项,因而将法律规定通过当然推理适用于该事项,就没有字面规定而言,并非法律解释而是法律推理。 当然推理是两个事物之间存在当然之理,因而可以将其中一个事物与另外一个事物同等对待。法律上的当然推理是指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基于法律的已有规定与待决案件之间存在当然之理,因而可以将法律的已有规定扩展适用于待决案件的法律推理方法。在民法领域,可以将当然推理确定为一种法律漏洞的填补方法;然而对于刑法来说,基于罪刑法定原则,入罪的当然推理应在禁止之列。至于出罪的当然推理或者其他有利于被告人的当然推理,仍然具有存在的正当性。 当然推理是以当然之理为根据的。我国学者认为这里的当然之理是指依形式逻辑或者事物属性的当然道理。因此,当然之理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形式逻辑上的当然道理;二是事物属性上的当然道理。我国学者指出:“所谓形式逻辑上的当然道理,是指从逻辑上讲,刑法规定所使用的概念当然包含被解释的概念,二者之间存在着种属关系。事物属性上的当然道理有两种情形:一是‘入罪,则举轻以明重’,二是‘出罪,则举重以明轻’。”在上述两种当然之理中,形式逻辑之当然是指概念之间的种属关系。例如刑法规定了汽车,当然包括小轿车,此为当然解释。然而,这种依据概念之间的种属关系对刑法进行解释,应当属于语义解释而非当然解释,更不可能是当然推理。至于事物属性之当然,即轻重相举的两种情形,则确实属于当然推理,但在刑法中能否采用,还要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应当具体分析。 当然推理作为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形进行规范填补的方法,如何将当然推理与类比推理相区分,是一个在界定当然推理的时候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刑法教义学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当然推理是类比推理的特殊类型。例如德国学者指出:“(类比推理)的一个特例是‘argumentum a minore ad maius’,即所谓‘举轻明重推理’(Erst-recht-Schluß)。‘举轻以明重’推理一般是针对特定法律后果的前提条件而言。”按照上述论述,当然推理具有类比推理的性质,前者只不过是后者的一种特殊情形。此外,德国学者还指出:“正面推理(即当然推理——引者注)基于这样的考虑:如果某个规范的法政策依据(规范目的)在法律没有规定的事实中比在法律有规定的事实构成中更加明显,那么类推适用就总是合理的。”在此,德国学者将当然推理归之于类推适用,因而其基础是类比推理。当然推理和类推适用的关系也被德国学者称为是一种亲缘关系,只不过类推是建立在两个事物之间具有类似关系的基础上,而当然推理则对事实构成A应赋予法律后果R,那么如果该规则的法律理由适用于与A相类似的事实构成B甚至能切合更高的标准的话,法律后果R适用于B则必然更加正确。因此,类推与当然解释之间确实存在密切的关联性。 将当然推理归入类比推理,从形式上看似乎合理。因为无论是基于事理的当然推理还是基于逻辑的当然推理,都采取了比较方法,并且建立在事物本质的观念之上,从而为由此及彼的推理提供了实质根据。然而,当然推理与类比推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区别,这种区别主要在于:类比推理的两个事物之间具有平行关系,并且主要借助于类似性概念建立一种对比关系。当然推理则具有上下关系,主要利用事物之间层级性概念建立一种对比关系。德国学者曾经指出,当然推理是一个可层升的概念和一个由此概念所形成的比较法规则作为基础,并列举了四种不同形式: (1)可层升的要素越是高度存在,法律效果就越是应该要发生(举轻以明重)。 (2)可层升的要素越是低度存在,法律效果就越不应该发生(举重以明轻)。 (3)可层升的要素越是高度存在,法律效果就越不应该发生(举轻以明重)。 (4)可层升的要素越是低度存在,法律效果就越是应该要发生(举重以明轻)。 可层升概念的本质特征在于该概念具有层级性,根据可层升概念所进行的推理属于当然推理。例如,举重以明轻的当然推理:“这个洞狗都能钻过去,猫也一定能钻过去。”在这个论断中,从狗能够钻过这个洞的事实,推导出猫也一定能钻过去的结论,属于举大以明小的当然推理。相反,举小以明大的当然推理:“这个洞猫都钻不过去,狗也一定钻不过去。”在这个论断中,从猫钻不过去这个洞的事实,推导出狗也一定钻不过去的结论,属于举小以明大的当然推理。由此可见,当然推理以层级性为推理的根据,这种层级既可以是大小,也可以是轻重或者其他层级差别。在上述判断中,是以猫和狗的体积大小作为根据的推理。 不同于当然推理以层级性作为推导根据,类比推理在通常情况下则是以类似性为推导根据的逻辑推理。例如:“这个洞牛都钻不过去,马也一定钻不过去。”在这个论断中,从牛钻不过去这个事实,推导出马也一定钻不过去的结论。相反:“这个洞牛都能钻过去,马也一定能钻过去。”在这个论断中,从牛能够钻过去这个事实,推导出马也一定能钻过去的结论。在上述两个判断中,牛和马的体积大小具有类似性,因而属于建立在类似性的基础之上的类比推理。 尽管当然推理和类比推理在推理的根据上有所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是完全对立的。在某些情况下,当然推理和类比推理之间具有一定的重合性。为了阐明当然推理与类比推理的重合关系,我们以禁止牛马通过的交通规则适用于禁止骆驼通过到底是类比推理还是当然推理为例进行逻辑分析。牛马与骆驼都是动物,就此而言具有一定的类似性。如果将这一点确定为逻辑推理的根据,那么就是类比推理。但如果将轻重的层级性引入考量,骆驼的体积和重量都要超过牛马,因而就对交通的妨碍程度来说,骆驼要大于牛马,既然牛马都要禁止,则骆驼更要禁止,按照这一逻辑推论,则属于当然推理。然而,上述推理属于类比推理和当然推理的竞合,即同时具有类比推理和当然推理的属性。但对比这两种推理,当然推理显然更具有说服力。因而,将上述推理归入当然推理更为合理。由此可见,当然推理并不是与类比推理相对立的,但当然推理具有不同于类比推理的根据,应当将其单独确定为一种推理方法。 在某些情况下,当然推理也被译为正面推理或者正当推理,有两种结构上相同的表现形式,即以小推大和以大推小;与之相对的反面推理或者反向推理是指如果法律对某一生活事实没有作出规定,就可以认为立法不愿意对此做出调整,因此有意保持沉默。之所以说反面推理具有推理的性质,是因为在反面推理中具有由此及彼的推导过程,这里的“此”是指法律的既有规定,而这里的“彼”则是指法律没有规定事项。因此,反面推理的具体过程可以描述为:从法律规范赋予某种事实情形以某个法律后果推导出这一后果不适用于法律规范未规定的其他事实情形的结论。换言之,如果法律规定的情形会导致某种后果,则法律未规定的情形就不会有该种后果。例如,从形式上看,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反向推理就可以得出结论:只有法律明文规定的行为才构成犯罪,这似乎是一个反面推理的适例,然而,关键在于对该反向推理内容如何正确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各国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通常只是规定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然而,我国《刑法》则在前半段还规定了犯罪有明文规定的应当依法定罪处刑。因此,我国学者将《刑法》第3条前半段界定为积极的罪刑法定,将后半段界定为消极的罪刑法定。但即使是反向推理,也不能得出法律有明文规定就应当定罪处刑的含义。这是因为,罪刑法定原则中的“罪”并不是通常语义上的犯罪,而是指符合构成要件的情形。因此,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是指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则不符合构成要件,既然不符合构成要件当然也就不可能构成犯罪。但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中反面推理出来的结论,则只能是法律有明文规定的行为必然符合构成要件。但符合构成要件的未必构成犯罪,因为是否构成犯罪,除了需要考察构成要件该当性以外,还需要考察违法性和有责性。正如我国学者指出:“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并不能反向推导出‘法有明文规定必为罪’,超法规的违法或阻却事由可以成为出罪事由,而法律明文规定的犯罪仍可以经由价值判断出罪。”确切地说,这里的法律明文规定的犯罪仍可以经由价值判断出罪,应当理解为:符合法律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可以经由价值判断出罪。由此可见,反向推理在某些情况下对于理解法律规定具有参考价值。正面推理的根据是正当性,因此也称为正当根据。这里的正当性也就是理所当然,因此,正面推理与当然推理虽然表述有别然而含义相同。 当然推理不仅适用于法律文本的内容推理,而且可以适用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和论证说理。因此,作为一种法律推理方法,当然推理的适用场景是较为丰富的。当然,当然推理主要还是适用于对法律文本的分析。在民法适用中,当然推理是一种法律漏洞填补的方法。在刑法适用中,由于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运用当然推理对法律文本进行分析时存在诸多限制。 在司法实践中,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的时候,往往采用当然推理的方法,因此,案件事实的当然推理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案件事实的当然推理,是指基于当然之理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在通常情况下,案件事实的认定是基于客观存在的证据,没有证据也就没有案件事实,这是证据裁判的基本规则。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对于案件事实也可以基于已然的案件事实与待证的案件事实之间的当然之理进行证明,以此作为案件事实认定的补充方法。然而,对于案件事实采用当然推理认定时,需要十分谨慎,避免发生事实认定的错误。例如付某印涉嫌故意杀人罪,在本案的裁判说理中,法官对单纯碾压脚部的明知与碾压他人身体的明知进行对比,认为既然对单纯碾压脚部具有明知,那么,对碾压他人身体更应具有明知。这里采用的就是举轻以明重的当然推理方法,由此证明被告人对碾压他人身体应当具有明知。尽管这种当然推理在逻辑上能够成立,但其结论的可靠性则存在较大的疑问。其实,在上述当然推理中,法官列举了被告人驾驶涉案车辆已有数年,对车重明确认知等客观事实,因而该推理本身又具有一定的推定的性质。这里应当指出,推理与推定是不同的:推理是基于逻辑关系所进行的一种推理活动,而推定则是基于事实关系所进行的一种证明活动。也就是说,两者在推断的根据上有所不同。评论意见认为,上述对明知的当然推理没有体现出法律上的评价意义。也就是说,当然推理应当以行为可能造成的结果具有明确的预见性这一构成要件要素而展开,具有规范上的关联性。应该说,这一评论还是具有针对性的。明知虽然是一个事实问题,但这种事实并不是裸的事实而是具有规范性的构成要件事实。因此,对案件事实的当然推理或者推定,都不能脱离规范要素。 裁判说理也经常采用当然推理的方法,这里的裁判说理中的当然推理是指在对定罪量刑的根据进行论证的时候,为了证明裁判结果的正当性,通过当然推理提供裁判理由。裁判说理中的当然推理往往存在于裁判文书之中,它对于强化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具有一定的功能。当然,在裁判说理中,当然推理的方法运用是否适当,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例如王某先涉嫌故意杀人案,法官在评价吸毒者是否应当负刑事责任时指出:“尽管我国刑法并未明确规定吸食毒品致精神障碍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明确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喝酒属于合法行为,醉酒后犯罪尚且要负刑事责任,吸毒本身就是违法行为,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当然解释,吸毒后犯罪更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本案所涉及的论题是吸食毒品致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问题,对此我国刑法确实没有规定。然而,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了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能力的精神障碍者不负刑事责任。但是,本案丧失刑事责任状态是吸毒造成的,对此被告人是否适用无责任能力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呢?这里涉及原因自由行为的法理。原因自由行为的法理是丧失责任能力的人不负刑事责任原则的一种例外。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彭某故意杀人案,就涉及吸毒影响责任能力而实施杀人行为之定性问题,该案也与原因自由行为的法理适用相关。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对于原因自由行为的法理并不熟悉,因而不能作为论证的法理根据。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以我国刑法关于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规定作为当然推理的前提。在某种意义上,从该规定中,可以推导出原因自由行为的法理。因此,法官基于吸毒的人犯罪较之因为合法饮酒导致醉酒的人犯罪,在事理上更重,从而得出结论:醉酒的人犯罪都应当负刑事责任,那么,吸毒的人犯罪的,更应当负刑事责任。应该说,虽然上述案例是可以采用原因自由行为的法理进行说理的,因为法官不能运用该法理,因而通过举轻以明重的当然推理为本案的裁判结论进行说理,虽然略显粗糙,但也难能可贵。 论辩说理中的当然推理,对于刑事辩护活动来说也能够发挥重要的论证功能。刑事辩护当然是依法辩护,因此,法律规定是辩护的主要根据。然而,法律规定并不是无所不在的,在某些情况下存在法律规定的缺失,此时就需要论辩说理,也就是基于法理或者事理而为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提出辩护理由。当然推理作为一种说理的方法,可以使论辩说理的结论更容易被司法人员所采纳。例如某个案件被告人被指控的行为是非国家工作人员挪用公司物品归个人使用,公诉机关以该物品具有可兑现价值为由,并以等价的资金数额追究被告人挪用资金罪的刑事责任。辩护人在法庭就以举重明轻的方法提出辩护理由:“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国家工作人员挪用非特定公物能否定罪的批复》(下称‘《批复》’)中规定:‘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挪用公款罪中未包括挪用非特定公物归个人使用的行为,对该行为不以挪用公款罪论处。’虽然在挪用资金罪的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中未提及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如何定性,但在对廉洁性要求更高的国家工作人员都不入罪的情况下,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定罪显然不当。”最终法院采纳辩护人意见,判决确认被告人不构成挪用资金罪。在以上案例中,对于挪用公物的行为是否应当以挪用公款罪论处?既然刑法规定的挪用公款并没有对挪用公物作出规定,如果仅仅从字面来看,挪用公物行为不能以挪用公款罪论处。但公物同样具有财产价值,只不过是财产的不同形态。因此,如果采用基于事物本质的实质判断,就会得出对挪用公物的行为应当以挪用公款罪论处的结论。当然,这种判断的方法是类推解释还是扩大解释可能存在争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批复》只是对挪用公物行为不能定罪的规定,而非国家工作人员挪用单位财物的行为还需要辩护人对能否适用《批复》进行充分的论辩说理。值得肯定的是,在说理中辩护人采用了当然推理的方法,既然对廉洁性要求更高的国家工作人员的挪用公物行为都不入罪,那么,对非国家工作人员挪用单位财物的行为更不应入罪。这种举重以明轻的当然推理得出的结论被法院所接受,是一个在刑事辩护活动中正确运用当然推理获得正面效果的案例,这也充分说明当然推理在刑辩活动中大有用武之地。 事理上的当然推理,是指基于事理所展开的推理方法。然而,在刑法中,并不是所有的当然推理都是能够采用的。毫无疑问,刑法中当然推理的适用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因此,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当然推理,是被法律所禁止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事理上的当然推理是法律所禁止的推理方式,不能在刑法适用中采用。 以事理为根据的当然推理,是当然推理中一种较为常见的方法。例如在当然推理中,经常涉及以大推小或者以小推大情形。这里的事项之间的大小关系是客观的,判断起来较为确定,这就为当然推理提供了确定的根据。在刑法中,事理上的当然推理是指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以刑法规定与待决案件之间的事理为根据而予以入罪或者出罪。这种事理上的当然推理往往表现为举轻以明重。德国学者指出:“如果基于法律目的而作出合乎评价的法律后果适用于权重更小的事项,那么该法律后果更应该适用于评价权重更大的、法律却没有规定调整的事项。”在此,德国学者明确将法律没有规定作为基于事理根据之当然推理的前置条件。 对事理上之当然的理解,关键在于如何界定事理。本文认为,这里的事理是指事物之理,它与情理存在某种区分。如果说情理具有一定的主观意志的性质,那么,事理就具有一定的客观规律的属性。因此,事理更能够反映两个事物之间的对比关系。事理是基于事物性质所产生的道理,具有一定的本然性。在某种意义上说,事理之当然推理是根据事物之本质所进行的一种推理。 我国古代在审理法无明文规定的案件比附援引类似的规范时,通常采用举轻以明重的方法。例如《唐律·名例·断罪无正条》:“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这里的举轻明重是指,刑法将轻行为规定为犯罪,虽然对重行为没有规定为犯罪,但根据举轻明重原则,对重行为可以援引对轻行为的规定加以入罪。我国学者将这种规定称为轻重相举之法,指出:“此条断罪轻重相举之法。此制之实质,乃以目的论之方法,对律条进行合理之解释。……轻重相举之法,就性质而论,属于比附断罪。比附断罪,即当罪人所犯律无正条时,得比类似之律条或附以往之判例而决之。”在此,我国学者将轻重相举之法界定为是比附断罪,同时又认为是基于目的论之解释,这两个见解是互相抵牾的。其实,比附断罪具有类推的性质。例如,如果轻行为和重行为之间存在类似关系,则举轻以明重就是一种类推。如前所述,将禁止牛马通过的交通规则适用于禁止骆驼通过的情形,牛马和骆驼是不同类型的动物,交通规则只是对牛马作了禁止性规定,是否禁止骆驼通过属于交通规则并无明文规定的事项,因此只有通过对禁止牛马通过的交通规则进行类推,才能将禁止牛马通过的交通规则适用于禁止骆驼通过。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牛马通过与骆驼通过这两者之间,不仅具有轻重行为之分,而且具有类似的关系。因此,可以将上述情形解释为类比推理与当然推理的竞合。由此可见,举轻以明重并非都是类推,只有在轻重行为之间存在类似关系的情形下才是类推。也就是说,当然推理不一定都是类推,如果两者之间没有类似关系而具有轻重关系,则属于当然推理。在某种意义上说,轻重相举的当然推理较之类比推理更具有逻辑推导的理由。 事理上之当然推理,虽然不是类推,但它是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前提的,通过事理关系而将法律规定适用于待决案件。因此,在刑法适用中,事理上之当然推理其实是一种将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入罪的情形,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适用中不得采用。 在我国刑法中对于事理上之当然推理的适用存在一定的争议,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如何判断法律规定与待决案件之间的关系。如果认为待决案件属于法律有规定的情形,则不能认为是事理上之当然推理。反之,则应当认定为是事理上之当然推理。 我国司法解释中也存在采用这种事理上的当然推理的情形。例如2004年11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关于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以火药为动力发射弹药的大口径武器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高检研发〔2004〕第18号)(下称“《答复》”)规定:“对于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以火药为动力发射弹药的大口径武器的行为,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以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枪支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枪支的概念,我国《枪支管理法》第46条做了明文规定。那么,上述《答复》所规定的“以火药为动力发射弹药的大口径武器”究竟何指呢?根据文字表达,这是指大炮。因此,《答复》的含义是:对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大炮的行为,以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枪支罪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典型的举轻以明重的入罪的当然推理,其根据在于在处罚必要性增加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可以突破法律文本的字面含义,按照事物本质对法律规定进行扩张于语义范围之外的适用,这是实质思维的必然结果。那么,《答复》的规定到底是法律解释还是关于法律适用的指引性规定?显然,枪支与大炮是两种不同的事物,立法机关只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枪支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没有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大炮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大炮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为枪支。因此,如果以刑法的明文规定作为入罪根据,大炮就不可能通过解释而获得定罪依据。 所以在此涉及的是如何适用法律问题而不是法律解释问题,是类似于填补漏洞的一种法律续造。如前所述,如果立法机关欲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大炮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只要采用武器一词取代枪支即可。但立法机关并没有采用这个方案,显然,立法机关并不是遗漏了大炮,而是认为没有必要将在现实生活中极为罕见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大炮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然而,一旦出现了这种行为,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就不能入罪。这也正是罪刑法定原则所具有的限制机能。但在实质理性的影响下,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却通过法律续造的方式认定为犯罪,这是明显不妥的。因为扩大解释是在语义范围内,从通常语义扩大到边缘语义,由于边缘语义没有超越语义边界,因此符合同一事物的本质。例如关于枪支,如果是假枪当然可以排除在枪支之外。那么,仿真枪能否解释为枪支呢?对此,公安部《关于对以气体等为动力发射金属弹丸或者其他物质的仿真枪认定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利用气瓶、弹簧、电机等形成压缩气体为动力、发射金属弹丸或者其他物质并具有杀伤力的‘仿真枪’,具备制式气枪的本质特征,应认定为枪支,并按气枪进行管制处理。”枪支在通常情况下是指制式枪支,以及能发射制式弹药的非制式枪支(包括自制、改制枪支)。仿真枪是一种玩具,不是按照枪支的使用目的生产、制造的,就此而言,似乎可以将仿真枪排除在枪支概念之外。但某些仿真枪具备枪支的杀伤性能,在这种情况下,仿真枪具有枪支的本质特征。本文认为,将具备枪支性能的仿真枪解释为枪支,是一种典型的扩大解释。因为虽然仿真枪在通常含义上不能等同于枪支,但在仿真枪具备杀伤力的情况下解释为枪支,并没有超出枪支的语义边界。与之不同的是将大炮解释为枪支,这是明显超出枪支语义范围的,因而不是解释而是法律续造。因为虽然大炮与枪支都属于武器,但武器是大炮与枪支的上位概念,不能由此得出大炮等同于枪支的结论,否则会得出荒谬的结论,例如牛与马都属于动物,因此牛等同于马,这种推理是难以成立的。大炮虽然也具有杀伤力,甚至杀伤力大于枪支,但大炮和枪支是两种不同的武器,两者在构造上存在明显的区别,不能归属于同一事物。 如果说,上述只是对个别事项基于事理上的当然之理所进行的当然推理,其影响尚且有限,那么,在以下涉及对国家机关证件的司法解释中,基于事理上的当然之理所进行的当然推理,则涉及对刑法规范的较大范围的理解,因而更值得关注。我国《刑法》第280条第1款规定了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那么,这里的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是否包括伪造、变造的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呢?这个问题对于伪造、变造来说,似乎是一个伪问题,因为作为伪造、变造对象的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当然是真的。对于假的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根本就不存在伪造、变造的问题。然而,对于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来说,则存在是否包括买卖假证件,即伪造、变造的国家机关证件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1998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下称“《决定》”)第2条将买卖伪造、变造的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行为规定为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由于《决定》的规定属于立法,则上述规定当然具有法律效力。那么,这一规定能否扩展及其他条款呢?这里要分析《决定》上述规定的性质,应该说,这一规定属于类推立法而非正常立法。也就是说,如果是正式设立罪名,应该设立买卖伪造、变造的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因为买卖伪造、变造的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并不符合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的构成要件,但《决定》却将买卖伪造、变造的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行为规定以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论处。因此,该规定具有立法类推的性质。类推虽然在司法活动中是被禁止的,但在立法中采用类推方法则是允许的,而且我国刑法的立法类推解释也并不罕见。可以说,这种类推立法具有法律拟制的性质,属于一种例外规定。此后,1999年6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买卖伪造的国家机关证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问题的答复》(下称“《答复》”)指出:“对于买卖伪造的国家机关证件的行为,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可适用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追究刑事责任。”《答复》的内容是将《决定》仅适用于买卖伪造、变造的海关签发的报关单、进口证明、外汇管理部门核准证件等凭证和单据或者国家机关的其他公文、证件、印章的具体场景的行为,扩展解释为所有买卖伪造的国家机关证件的情形。在解读上述《答复》时,相关人员认为,买卖伪造的国家机关证件的危害性比买卖真实的国家机关证件还要严重,虽然刑法没有规定,但既然刑法规定伪造国家机关证件构成犯罪,买卖伪造的国家机关证件行为同样可以按照犯罪处理。这是属于法律规定的应有之义,司法机关可以依法予以处理。上述解读已经明确指出,将买卖伪造的国家机关证件行为以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论处,是以法律没有规定为前提的,因此该《答复》不可能是一种司法解释,而是一种当然解释,其实就是一种基于事理上的当然之理所进行的当然推理。我国学者指出:“当然解释试图通过逻辑推演来确定规范的范围,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此过程中,最终的结论仍然需要提供规范目的考察来加以确定。正是由于对规范目的和所谓的事物属性的认识有着不同,造成解释的当然性也处在争议之中,使得某一解释并不为人们当然地视之‘当然’之意。” 此外,例外规定不得进一步扩张其适用范围,这也是一个基本原理。正如德国学者指出,“例外的规定不允许延伸”这一定理应该非常谨慎地运用,而由立法者偶尔提出的禁止类比必须被承认是允许的类比的界限。因此,对于刑法采用拟制的方法作出的例外规定,更不能进行事理上的当然推理。因为如果允许这种当然推理,则其效应会波及其他类似场景。例如如果买卖伪造、变造的国家机关证件行为可以构成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依此类推,则倒卖假香烟的行为可以构成非法经营罪;倒卖假文物的行为也可以构成倒卖文物罪;贩卖假毒品的行为也可以构成贩卖毒品罪。甚至可以推而广之,只要符合举轻以明重的原理,则可以将刑法规定的所有物品都解释或者推理为包括假物品,这明显是荒谬的。 如果说具有入罪性质的不利于被告人的事理上之当然推理不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因而不得采用,那么,事理能否成为出罪的当然之理呢?回答是肯定的。在刑法中,我们应当坚持入罪以法,出罪以理的司法理念。这里的入罪以法就是将某个行为认定为犯罪,必须要有法律的明文规定,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应有之义。与之不同,某个行为即使符合构成要件,如果具有某种事理上的根据,则完全可以出罪,这就是出罪以理。例如,举轻以明重的当然推理就可以成为出罪根据。这里的举轻以明重,是指如果按照法律规定具有更大权重的事项都没有引发特定的法律后果,那么更小权重的事项就更不会引发特定的法律后果。例如《唐律疏议》规定:“其应出罪者,依贼盗律:‘夜无故入人家,主人登时杀者,勿论。’假有折伤,灼然不坐。又条:‘盗缌麻以上财物,节级减凡盗之罪。’若犯诈欺及坐赃之类,在律虽无减文,盗罪尚得减科,余犯明从减法。此并举重明轻之类。”在此,“杀”与“伤”之间存在轻重之别,既然杀死不构成犯罪,那么,伤害当然更不应当以犯罪论处。这就是通过事理上的当然之理而出罪。此外,“盗”与“骗”之间同样存在轻重之分,那么,既然窃盗和强盗可以减轻处罚,则诈骗更应当减轻处罚。这是通过事理上的当然之理而减轻。由此可见,事理上的当然之理既可以成为入罪的根据,又可以成为减轻的根据。 从上述举重以明轻适用于出罪的场景来看,实际上隐含着出罪需要法律明文规定的观念。然而,这一观念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相抵触。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也即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就不能作为犯罪论处。比如正当防卫属于违法阻却事由,这是由刑法总则规定的,它适用于所有案件。而且,违法阻却事由可以分为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和非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在非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的适用中,不仅没有刑法分则规定,而且也没有刑法总则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可以出罪。正如日本学者指出:“对在有利于行为人的方向进行的解释,不受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实际上也可以从超法规的观点广泛地承认违法性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应该说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不允许进行对犯人不利的类推。但是,不禁止有利的类推。”由此可见,举重以明轻而出罪,作为一种司法规则,它是从罪刑法定中引申出来的必然结论。
当然推理之当然,除了事理之当然以外,还包括逻辑之当然。在事理之当然的情况下,两个事项之间只是存在大小、轻重之分,根据大小、轻重之对比获得一定的结论。在这种当然推理作为入罪根据的时候,实际上是将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通过事理之当然推理而予以入罪,从而扩张了刑法规定的适用范围。但如果当然推理之当然,不是事理之当然而是逻辑之当然,那么,并不排除当然推理可以作为入罪的根据,因而为法律所允许。 逻辑上之当然推理中的逻辑是指推理的根据,即以法律规定与待决案件之间具有一定的逻辑递进关系作为推理的根据。递进关系通常是指语词承接上的逻辑关系,这种关系不仅要求内容上的逻辑性,还要求使用恰当的关联词语来表达这种进阶关系。当递进关系用于描述两个事项之间的关系时,是指后一事项比前一事项在程度、范围、深度等方面的增强或减弱。在具有递进关系的两个事项之间,后一个事项是从前一个事项演变而来,因而虽然前后是两个不同的事项,但前一事项与后一事项在逻辑上具有衔接关系,后一事项较之前一事项具有程度上的对比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在具有递进关系的两个事项之间,后一个事项涵盖前一事项。例如,甲某经过A地抵达B地。对于甲某来说,身处B地时,就表明其已经到过A地。因此,甲某到达B地这个事实涵盖了到过A地这个事实。 德国学者库鲁格曾经将法律条文之法律要件(M)与法律效果(P)的关系分为三种情形:第一是外延的包含,即有M就有P。从逻辑上说,M法律要件是P法律效果的充分条件。第二是内涵的包含,即无M法律要件即无P法律效果的必要条件。第三是相互的包含,即有M则有P,无M则无P,MP相重叠的情形。从逻辑上说,M法律效果是P法律效果的充分条件及必要条件。在上述三种关系中,第三种情形相互包含是概念之间的同一关系,第一种和第二种则是概念的外延的包含关系与概念的内涵的隶属关系。这里的包含关系,也可以称为隶属关系,但外延的隶属关系与内涵的隶属关系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分。 外延的隶属关系是指两个概念之间具有种属关系,属概念隶属于种概念。因此,外延的隶属关系是以两个概念之间存在涵摄关系为前提的,法律对于种概念有规定,该规定当然适用于属概念。在这个意义上说,法律关于种概念的规定等同于对属概念的规定。例如法律对武器规定的法律效力及于枪、炮等与之具有种属关系的所有类别的武器。因此,凡是对武器的规定,均可视为对具体武器的规定。反之则不然。法律对具体武器的规定,不能视为是对所有武器的规定。例如法律规定制造枪支构成犯罪,并不等于规定制造其他类别武器也构成犯罪,更不等于规定制造所有武器都构成犯罪。因为武器涵摄各种类别武器,具体类别武器却并不涵摄一般类别武器。外延上的隶属,在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概念中是指特别法与普通法之间的法条竞合关系,简称特别关系。在特别关系的概念之间,具有种属关系。内涵的隶属关系是指两个概念之间具有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部分概念被整体概念所涵盖。法律对于整体概念有规定,但对于部分概念没有规定的,法律对整体概念规定的法律效力并不当然适用于部分概念。例如,在结合犯的情况下,包含了所结合的两个犯罪的内容,但该规定只适用于整体概念,并不适用于部分概念。反之,法律对部分概念有规定,但对整体概念没有规定的,法律对部分概念的规定不能适用于整体概念。下面分别对外延的隶属关系与内涵的隶属关系进行分析。 外延的隶属关系是一种种属关系,假设种概念是A,属概念是B, B是A外延的一部分。假设: 上述外延的隶属关系的罪名概念之间具有三种情形:第一,刑法将种概念之行为和属概念之行为同时规定为犯罪,行为人实施了属概念之行为,则形成特别法与普通法之间的竞合关系。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以特别法之罪名论处。例如盗取枪支罪与盗窃罪,盗窃罪是普通法规定,盗窃枪支罪是特别法规定,盗窃罪的外延包含盗窃枪支罪。在行为人实施盗窃枪支行为的情况下,其行为同时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应以盗窃罪论处。第二,刑法将种概念之行为规定为犯罪,属概念之行为并未规定为犯罪,则属概念之行为应以种概念之罪名论处。例如刑法规定了盗窃罪,但并未规定盗窃枪支罪。因为盗窃枪支罪在外延上隶属于盗窃罪,则对盗窃枪支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第三,刑法未将种概念之行为规定为犯罪,但将属概念之行为规定为犯罪,则应以属概念之罪名论处。例如在刑法规定了盗窃枪支罪,但并未规定盗窃罪的情况下,只能对盗窃枪支行为进行处罚,对盗窃其他财物的行为进行处罚于法无据,也就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 内涵的隶属关系是一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假设整体概念是A,部分概念是B, B是A内涵的一部分。假设: 上述内涵的隶属关系的罪名概念之间具有三种情形:第一,刑法将整体概念之行为和部分概念之行为同时规定为犯罪,行为人实施了整体概念之行为,则形成整体法与部分法之间的竞合关系。根据整体法优于部分法的原则,应以整体法之罪名论处。例如抢劫罪与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是整体法规定,故意杀人罪是部分法规定,抢劫罪涵盖故意杀人罪。在行为人实施抢劫杀人行为的情况下,故意杀人行为被抢劫罪所吸收,按照整体法优于部分法的适用原则,应以抢劫罪论处,故意杀人行为不再单独定罪。第二,刑法将整体概念之行为规定为犯罪,部分概念之行为并未规定为犯罪,则部分概念之行为应以整体概念之罪名论处。例如刑法只是规定了抢劫罪,但并未规定故意杀人罪的情况下,行为人实施了抢劫杀人行为的,应以抢劫罪论处。因为故意杀人行为虽然没有单独设立罪名,但其行为被抢劫罪所涵盖,因而抢劫罪已经包含了对故意杀人行为的评价,应以抢劫罪论处。第三,刑法未将整体概念之行为规定为犯罪,却将部分概念之行为规定为犯罪,应以部分概念之罪名论处。例如在刑法只是设立了故意杀人罪,并未设立抢劫罪的情况下,对于抢劫杀人行为可以按照故意杀人罪处罚。因为在这种整体法与部分法的隶属关系中,整体与部分之间作为实体内容是可以进行分割的。因此,在上述抢劫罪涵盖故意杀人罪的内涵隶属关系中,虽然刑法对抢劫罪没有规定,对抢劫罪中的部分行为——故意杀人行为,却仍然可以按照故意杀人罪处罚。因此,在两个概念之间具有涵盖关系的情况下,概念之间具有实体上的独立性,对整体法的规定不等于对部分法的规定,而部分法却可以作为整体法的一部分,对整体法中具有竞合关系的部分行为进行评价。基于部分法与整体法的重合部分的竞合关系,将刑法对部分法的规定适用于整体法中的重合部分,就是基于逻辑上的当然之理所进行的当然推理。 在上述情形中,涉及逻辑上的当然推理的情形是:刑法未将整体概念之行为规定为犯罪,却将部分概念之行为规定为犯罪。但从逻辑意义上分析,整体概念之部分行为与部分概念之行为存在重合性,而且整体概念之行为与部分概念之行为之间具有轻重之关系,因而按照举轻以明重的当然推理,将刑法没有规定的整体概念之行为以部分概念之罪名论处,并非刑法解释之结果,而是当然推理之结论。例如抢劫罪与抢夺罪之间存在轻重之关系,而且抢夺行为是抢劫行为之部分。如果刑法只是规定了抢夺罪,但未规定抢劫罪,因为抢劫罪的夺取行为完全符合抢夺罪的构成要件,因而对刑法未规定之抢劫罪以抢夺罪论处,这是根据逻辑上之当然推理得出的必然结论,而且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将这种基于当然之理的推理方法适用于法律适用,可以解决法律规范的适用范围或者效力问题。例如德国学者在论述当然推理时指出:“在法律科学中,通常会由某个更广泛之法律规范的效力推导出某个不那么广泛之法律规范的效力。这种论证方式在使用时通常带有短语‘更加’这里提到的论证方式——以并非总是统一和清晰区分的方式——被称为举轻以明重(以小推大)、当然推理或者举重以明轻。”在此,德国学者将当然推理称为是一种论证方法,因而不同于解释方法。例如《唐律·贼盗律》规定:“谋杀期亲尊长,皆斩。”对此,《唐律疏议》注曰:“案贼盗律,谋杀期亲尊长皆斩,无已杀、已伤之文。如有杀伤者,举始谋是轻,尚得死罪,杀及谋而已伤是重,明从皆斩之坐。又例云:殴、告大功尊长、小功尊属,不得以荫论。若有殴、告期亲尊长,举大功是轻,期亲是重,亦不得用荫,是举轻明重之类。”这是《唐律疏议》对举轻以明重的理解,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刑法中的举轻以明重规则具有参考意义。《唐律》的上述规定,涉及“谋杀”与“已杀”之间的轻重相举关系。按照《唐律》规定,“谋杀”,即预谋杀害期亲尊长的行为应当处以斩刑,然而对比“谋杀”性质更为严重的“已杀”行为如何处理,《唐律》却未做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举轻以明重的规则,既然“谋杀”都处斩刑,那么,对预谋以后继而付诸实施的“已杀”行为,当然更应当处以斩刑。但这个意义上的举轻以明重并不是类推而是当然推理。因为“谋杀”与“已杀”之间并不存在类似关系,但却存在轻重关系。在上述情况下,经过预谋阶段而递进到杀人之实行阶段,并且造成死亡结果。因此,重行为(已杀)中已经涵括轻行为(谋杀)。因此,对刑法没有规定的重行为援引刑法对轻行为规定的处罚,这是当然之理,因而是逻辑上的当然之理。在刑法教义学中,通常认为行为经过预谋或者预备以后,继而发展到实行阶段,则预谋或者预备的要素被实行行为所吸收,对预谋或者预备的要素不再另行独立评价。 在此,我们需要对这里的刑法对重行为没有规定的蕴含进行细致的逻辑分析。其实,在上述情况下,刑法虽然对重行为没有规定,但对重行为所涵盖的轻行为有规定。也就是说,“已杀”涵盖了“谋杀”,因为“谋杀”是“已杀”的预备行为,经过预备而递进到实行行为,预备行为被实行行为所吸收。在这个意义上,重行为也完全符合轻行为的规定。对此,按照当然推理适用轻行为的规定是具有充分根据的。例如在上述《唐律》将谋杀期亲尊长皆斩的规定适用于已杀行为的情况下,在谋杀和已杀之间,后者包含前者,因为预谋杀害是指杀人的预备行为,已杀是指杀人既遂。从逻辑上说,已杀是经过谋杀达成的杀人既遂状态。因此,已杀涵盖谋杀。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举轻以明重的当然推理,对已杀行为适用谋杀之律条并无不当。由此可见,在两个事项之间存在递进关系的情况下,后者在逻辑上包括前者,因而尽管刑法对后者没有独立规定,但由于刑法对前者已经有规定,因而具备逻辑上的当然之理。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当然推理入罪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应当指出,在论述当然解释(即当然推理)的时候,我国学者认为逻辑上的当然是指逻辑上存在种属关系。我也曾经认为逻辑之当然是指概念之间存在递进或者种属关系。这里主要涉及具有当然关系的两个事项之间是否属于种属概念,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当然推理与语义解释之间的关系。对此,我国存在竞合说,这种观点认为:“就语义解释与当然解释的关系而言,可以说,在法律解释的过程中当然解释并非完全处于辅助地位,相反总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具体到种属关系而言,语义解释与当然解释有些许重合的部分再为正常不过,就像法条会产生竞合一样正常。”这种观点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语义解释与当然解释之间存在竞合,因此,两者并不完全互斥。本文认为,种属关系是概念之间的一种关系,种属概念可以分为种概念和属概念。其中,种概念是上位概念,属概念是下位概念,种概念包括属概念,属概念被种概念所涵括。因此,法律对种概念的规定可以适用于属概念。例如德国学者指出:“从对属于特定大概念的某一类案件有效的法规范中,可推论出,该法规范同样对属于这一大概念的其他案件有效。例如,行为人基于重大认识错误而不能将犯罪行为实施终了的,可免除刑罚(《德国刑法典》第23条第3款)的规定,可延伸至不能犯未遂。”在上述论述中,行为人基于重大认识错误而不能将犯罪行为实施终了的情形是未遂犯,不能犯未遂则是未遂犯的一种特殊情形。因此,未遂犯是种概念,不能犯未遂则是属概念。因此,刑法对未遂犯的规定,当然适用于不能犯未遂。在此,只要进行语义解释即可。又如,武器是种概念,它的外延较大,包括枪支、大炮以及其他种类的武器。因此,当刑法规定武器的情况下,当然可以从武器概念中解释出枪支、大炮等。在此,采用的只是单纯的语义解释方法,而并不需要采用当然推理。例如完全可以将枪支或者大炮直接解释为武器,在此并没有采用当然解释或者当然推理的空间。因为刑法规定的武器概念中已经包含了枪支和大炮的内容。但如果刑法并没有规定武器,而是规定枪支,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通过类推将大炮解释为枪支。在枪支和大炮之间并不存在种属概念的关系。当然,在枪支和大炮之间存在事理上的当然之理,在民法中可以采用事理上的当然推理。但在刑法只规定了枪支并未规定大炮的情况下,大炮属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形,就不能进行当然推理。 当然推理中的事理上之当然与逻辑上之当然的关系的界分,在法学方法论中存在两种情形:第一是具有事理上之当然但并不具有逻辑上之当然;第二是同时具备事理上之当然和逻辑上之当然。例如在将禁止牛马通过的交通规则适用于禁止骆驼通过的场合,具有事理上之当然,但并不具备逻辑上之当然。这种情形,不能否定其属于当然推理,只是在刑法适用中被禁止。因为对牛马通过的禁止并不等于对骆驼通过的禁止。在牛马和骆驼之间只是存在事理上之当然关系,但并不存在逻辑上之当然关系。换言之,对牛马通过的禁止并不等同于对骆驼通过的禁止。反之,在当然推理中如果存在逻辑上之当然,通常也就是会存在事理上之当然。因此,刑法所允许的当然推理不仅包含事理上之当然,而且包含逻辑上之当然,两者必须同时具备。 逻辑上之当然推理是以重行为涵盖轻行为为前提的,例如前述《唐律疏议》所规定的谋杀期亲尊长皆斩的规定,只是对谋杀作了规定,但并未对已杀、已伤的情形作出规定。因此,不能从《唐律》对谋杀的规定中解读出已杀、已伤的内容。在此,就不存在解释的空间。但已杀、已伤经过了谋杀的阶段,两者之间具有递进关系。因此,《唐律》对已杀、已伤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已杀、已伤其实涵括了谋杀的内容。因此,这里存在逻辑上之当然关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当然推理对已杀、已伤行为入罪,完全符合法律逻辑。在我国刑法中也存在这种需要通过当然推理加以明确法条含义的情形。例如《刑法》第277条第4款规定:“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这里的第1款规定是指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行为的规定,由于该款规定明确了以暴力、威胁为其行为方式,而第4款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而构成妨碍公务罪的,并不要求以暴力、威胁为其行为方式,因而在法条中立法机关规定第4款行为以“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为条件。在没有要求暴力、威胁为其行为方式的情况下,即使没有这一规定,从法律文本的含义来说,也不要求暴力、威胁方法。因此,我国学者认为第4款中“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不是真正的构成要件要素而是表面要素。那么,如果行为人采用暴力、威胁方法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的,应当如何定罪处罚呢?我国学者将这里的“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解释为“即使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以此为根据,完全可以对使用暴力、威胁方法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采用当然推理的方法,仍然以第4款规定论处。因为在以暴力、威胁方法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的情况下,涵盖了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的行为,因此具备逻辑上的当然事理。 在当然推理中,如何区分事理上的当然推理和逻辑上的当然推理,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本文认为,这种区分应当建立在对当然推理所涉及的轻重行为的内容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例如,我国《刑法》第329条规定了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本罪的行为是抢夺和窃取,但并没有规定抢劫。那么,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能否认定为抢夺国有档案罪呢?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能否从抢夺推导出抢劫呢?对此,我国刑法学界存在两种观点:肯定说认为,一个行为如果在符合法条规定要素的前提下超出了该法条的要求,也没有其他可适用的法条,则应适用该法条。例如《刑法》第329条规定了“抢夺”国有档案罪。倘若行为人以暴力相威胁“抢劫”国有档案,应该如何处理?从规范意义上说,抢劫行为已经在符合抢夺要件的情况下超出了抢夺的要求,既然如此,当然可以将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评定为抢夺国有档案罪。这种解释可谓当然解释,但同时是出于体系解释的考虑。在肯定说的论证中,明显是采用了举轻以明重的当然推理方法。否定说则认为,根据举轻以明重的传统法理对抢劫国有档案行为纳入抢夺国有档案罪处理,从而解决了因立法不足而导致的司法困难问题。但举轻以明重很容易导致类比定罪,如果在没有法条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仅根据类比就得出解释结论无疑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显然,否定说将这种举轻以明重的推理方法界定为是类推解释,因而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 在此首先要分析上述推理是否属于类比推理,也就是类推。本文认为,类推是基于类似关系,然而抢夺和抢劫之间并不存在类似关系,因为这两种犯罪的构成要件存在明显的差异。由此可见,对抢劫档案行为以抢夺档案罪论处归之于类推,并不符合类推的特征。那么,抢夺档案与抢劫档案只能是否存在逻辑上的当然关系呢?如果从《刑法》第329条的字面规定来看,确实只是规定了抢夺国有档案但却没有规定抢劫国有档案。应该说,将抢劫国有档案行为解释为抢夺国有档案,这是采用了举轻明重的推理方法。这种推理也就是当然推理。至于是否属于逻辑上的当然推理,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确定抢劫国有档案行为与抢夺国有档案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换言之,抢劫行为是否在逻辑上涵盖了抢夺行为?应当指出,前述抢劫罪与故意杀人罪之间的整体法与部分法之间的当然推理之原理也完全可以适用于抢劫档案罪与抢劫罪之间的关系分析。当然,抢劫罪与故意杀人罪的当然之理不是轻重程度之理,而是范围大小之理。抢劫罪的范围较大,其涵盖了故意杀人,因此基于适用于大范围的法律规定当然可以适用于具有内涵上隶属关系之小范围的罪名。抢劫档案罪与抢夺档案罪之间是轻重程度上的当然之理,并且两者之间存在行为方式上的涵盖关系,即抢夺行为隶属于抢劫行为,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刑法只规定了抢夺档案罪却没有规定抢劫档案罪,但在行为人实施抢劫档案行为的时候,对其中的抢夺档案行为完全可以通过抢夺档案罪的构成要件进行评价,因而属于逻辑上的当然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