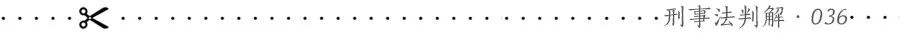申柳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猫王案”的判决译介
《刑事法判解》由北京大学法学院主办,陈兴良教授任主编,车浩教授任执行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发行。刊物关注刑事司法领域的实务问题,诚邀学界和实务界同仁赐稿。
公号&刊物来稿请至:xingshifapanjie@126.com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猫王案”的判决译介
by 申柳华
北京大学刑法学博士
德国被害人保护协会博士后研究人员
导读:本文原载于《刑事法判解》第13卷。文章详细地介绍了德国联邦法院“猫王案”的判决内容和理由,并就此案中所体现在间接正犯与教唆犯的区分问题在德国刑法学界的争议和发展进行了简述。“猫王案”是德国刑法学讨论间接正犯与教唆犯关系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经典案例。从中可以看出,国外刑法理论的发展,从判例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猫王案(Katzenkönigs-Fall)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1988年9月15日作出的判决。本案的核心争议点是:在犯罪工具者(Tatmittler)产生一个可避免的禁止认识错误(vermeidbare Verbotsirrtum)的情况下,如何区分间接正犯(mittelbare Täterschaft)和教唆犯(Anstiftung)。猫王案是德国学理讨论间接正犯与教唆犯关系的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标杆性案例,对后续理论和实务的发展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间接正犯;教唆犯;可避免禁止错误;共同犯罪;支配 * 本文原载于《刑事法判解》第13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为便于阅读,脚注从略。 猫王案(Katzenkönigs-Fall)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1988年9月15日作出的判决,即刑四庭1988年第352号(BGH vom 15.09.1988 - 4 StR 352/88)。一审法院为波鸿地方法院,提交最高法院审判的争议点是:在犯罪工具者(Tatmittler)产生一个可避免的禁止认识错误(vermeidbare Verbotsirrtum)的情况下,如何界定间接正犯(mittelbare Täterschaft)和教唆犯(Anstiftung)。 一 基本案情 地方法院以谋杀罪未遂判处被告人H和P终身监禁,被告人R九年有期徒刑并命令将其收容于精神病院。在上诉中,被告人指控该判决违反了实体法(materielle Recht);被告人H将其上诉请求限制在原判决内。最高法院否定了地方法院的判决,而被告人P和R的上诉没有成功。 被告人R与被告人H和P生活在一种受“神秘主义、虚幻认知和妄想(Mystizismus, Scheinerkenntnis und Irrglauben)”影响的“神经质的关系网(neurotischen Beziehungsgeflecht)”中。被告人H在P有意识的共同作用下,一起成功地使容易受影响的被告人R相信了:首先,H瞎编自己受到皮条客和恶棍的威胁,R应当扮演保护者的角色来保护H;二人再通过一些表演性的伎俩,使得R相信了“猫王”的存在——它数千年以来都是邪恶的化身,并威胁着世界。R由于受到其判断能力的限制,同时也为了争取到H的爱情,终于说服自己与H和P共同投入到反抗的猫王的战斗中。但是,他首先应当通过一些勇气的测试,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宣誓效忠于H;这样他将甘愿成为供H和P娱乐的工具。1986年中,当H得知自己前男友Udo N.结婚的消息,出于出于仇恨与嫉妒,她决定利用被告人R的迷信,由其杀死前男友的妻子Annemarie N女士。在P的默认下,为了除掉她的情敌,被告人H在被告人R面前表演道:由于R犯了很多错误,“猫王”要求将N女士作为人祭(Menschenopfer)献给他;如果R不在短限内完成这个献祭行为,他就必须离开H,并且整个人类或者数以百万计的人将会被“猫王”灭绝。R意识到这是谋杀,并徒劳地向摩西十诫中的第五条诫命(das fünfte Gebote)寻找出路。H和P则不断地指出,杀人的诫命对他无效,“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命他拯救人类”。在他对着H必须“以耶稣的名义”宣誓杀人之后,H又指出如果R违反了誓言,他“不朽的灵魂,将受到永恒的诅咒”。他决定实施犯罪行为。R饱受良心的折磨,但是衡量到 “通过牺牲N女士”,可以拯救“数以百万计的人于危险之中”,决定实施犯罪。在1986年7月30号深夜,R以买玫瑰为名义,来到N女士工作的花店中。按照P的建议,同时也在H.的同意之下,R利用P留下的 匕首,从后面刺向了毫无准备、没有防范的N女士的脖子、脸上和身体多处,以达到将其杀死的目的。由于看到多位旁人听到呼救赶来,R为了不被人认出,放弃继续行刺,逃离现场。但是他预计该被害人会死亡。实际上,N女士并未死亡。 二 法条索引 本案例中引用了如下德国刑法典中的法条: 第17条禁止的错误(§ 17 StGB):1 行为人行为时没有认识其违法性,如果该认识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则对其行为不负责任。2如该认识错误是可以避免的,则依照第49条第1款减轻处罚。 第20条精神障碍者的无责任能力(§ 20 StGB):行为人行为时,由于病理性精神障碍、深度的意识错乱、智力低下或者其他严重的精神疾病,不能认识行为的违法性、或者依照其认识而行为的,不负刑事责任。 第21条减弱的责任能力(§ 21 StGB):行为人认识行为违法性的能力或者依照其认识而行为的能力因第20条规定的某种原因而显著减弱的,以依照第49条第1款减轻其刑罚。 第23条未遂的可罚性第2款(§ 23 Abs. 2 StGB):(2)未遂可比照既遂减轻处罚(第49条第1款) 第24条中止第2款第1句 (§ 24 Abs. 1 S. 2 StGB):(1)1行为人自愿地放弃行为的继续进行,或者主动阻止其完成的,不因犯罪未遂而受处罚。2如果行为无中止犯的努力不能完成的,只要行为人自愿和认真努力阻止该行为的完成,那么应不予处罚。 第25条正犯(§ 25 StGB):(1)自己实施犯罪,或者通过他人实施犯罪的,以正犯论处。(2)多人共同实施犯罪的,均以正犯论处(共同正犯)。 第32条正当防卫(§ 32 StGB)(1)正当防卫不违法。(2)为使自己或他人免受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而实施的必要的防卫行为,是正当防卫。 第34条阻却违法性的紧急避险(§ 34 StGB):1为使自己或他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或其他法益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不违法,但须衡量两种冲突利益,即其所要保护的法益应明显大于所造成危害的法益。2仅在行为属于避免该危险的适当的措施的情况下,方可适用本条的规定。 第35条阻却责任的紧急避险 (§ 35 StGB):(1)1为使自己、亲属或其他与之关系密切的 人的生命、身体或自由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违法行为不负刑事责任。2在因行为人自己引起危险或因其处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而需容忍该危险的限度内,不适用该规定; 第49条特别的法定减轻理由第1款(§ 49 Abs. 1 StGB)(1)法律规定或允许可以本条减刑的,适用下列各项规定: 1、终身监禁时,代之以不低于3年的自由刑。 2、(1)有期自由刑的情况最高可以判处最高限度的3/4。(2)该标准同样适用于罚金刑中日额的最高数量。 3、被提高了的最底自由刑, 在最底自由刑为10年或5年的情形下,减至2年, 在最底自由刑为3年或2年的情形下,减至6个月, 在最底自由刑为1年的情形下,减至3个月, 在其他情形下减至法定最低刑。 第63条收容于精神病院(§ 63 StGB ):实施违法行为时处于无责任能力(第20条)或限制责任能力(第21条)状态的,法院在对行为人及其行为进行综合评价后,如果认为其还可能实施违法行为,对公众具有危险性的,可命令将其收容于精神病院。 第211条谋杀罪(§ 211 StGB):(1)谋杀者处终身监禁。 (2)谋杀者是指出于杀人嗜好、性欲的满足、贪财或者其他卑劣动机,以阴险、残暴或者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或意图实现或者掩盖其他犯罪行为而杀人的人。 三 判决理由 地方法院正确地判决所有被告人成立谋杀罪未遂之正犯。 (一)被告人R: 刑事法庭无法律错误地认定该被告人符合了用阴险的方法谋杀罪这一构成要件。R“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以杀人的故意,亲手刺向N女士”;并且他有意识地利用了N女士的不怀疑与无抵抗能力(Arg-Wehrlogsigkeit)的状态。谋杀的未遂行为已经完成,因为最后的刺杀行为实施完成之后,被告人相信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会发生(类似见:德国最高法院刑事判例汇编BGHSt 35, 90, 92.)。未遂行为不能免除刑罚,因为 被告人没有采取刑法24条第1款第2句规定的措施,努力阻止犯罪结果的发生。 地方法院也正确地认为,被告人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经咨询专家意见,刑事法庭确信,被告人并不弱智(schwachsinnig),也没有精神病。他的行为可能出于“高度异常人格”,这是一种“神经质的深度的扭曲和变形”的人格。刑事法庭进一步指出,他的这种状态导致了,他被“H 和P成功的说服”,在犯罪行为实施的阶段生活在“确信的幻想(Wahngewißheiten)”状态中。地方法院并没有把这种人格的画像(Persönlichkeitsbild)归属为刑法20条表述的构成要件。从他的实行行为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作为严重的其他异常精神病态人意义上的实施步骤。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被告人的理解能力(Einsichtsfähigkeit),因为他认识到杀人是被禁止的,并且他认识到事情的来龙去脉。被告人也没有丧失控制能力,他可以放弃犯罪行为的实施。由于被告存在着妄想和由其造成的病理上的感觉,刑事法庭认为可以考虑应用刑法21条中减弱的责任能力的规定。 被告人R不能援引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刑法典》第32条)的规定,因为如同他所意识到的那样,他和其他人没有受到一个现时的、来自被害人的违法侵害。根据刑法第34条,阻却违法的紧急避险也不存在,因为缺乏一种现实的、正在发生的危险。尽管R相信存在这样的一种危险。但是,他这种对“刑法第34条事实条件的认识错误”不能被认定为“符合构成要件的认识错误”。因为刑法第34条中作为前提的是,被保护的利益大于被损害的利益——这不适用于“生命对生命的衡量中” (相关案例:OGHSt 1, 321, 334;2, 117, 121; Dreher/Tröndle, 刑法教科书,第44版,第34 章,编码 10)。被告人错误地衡量了这种利益冲突,这也不能作为评价错误(Bewertungsirrtum)而阻却故意,而是符合刑法第17条规定的——可避免的禁止错误(相关评论. Lenckner in Schönke/ Schröder, 刑法教科书第 23版,第 34章,编码51; Dreher/Tröndle 上书第 34章,编码 18)。然后作为一名警察,考虑到其个人能力和良心上的不安所导致的幻想,以及可期待其向值得信任的人咨询,比如牧师,他应当可以认识到法律不允许以一个数量计量的人类的生命作为最高的价值。 刑事法庭同样正确地否定了被告人行为构成刑法第35条阻却责任的紧急避险规定的免责,因为行为人没有使家人或者其他亲近之人避免幻想中的危险的意愿(相关见: Hirsch , 莱比锡法律评论,第10版,第 35章,编码38)。他不担心自己的死亡,因为他相信H和P的瞎话,认为他已经活过多次,其灵魂将会重新回来;他并没有考虑过家人和其他亲近之人。 地方法院没有检验,被告人是否属于超法规事由的应用领域,是否可以适用刑法第35条超法规的阻却责任的紧急避险的规定(相关见:Lackner,德国刑法学第17版, 第 32节 Anm. 111 3m部分)。这并不能抵消被告人的罪责。这样的罪责排出事由或者排除刑法事由(相关见上面提到的Lackner教科书)只有被告人认识到紧急避险的状态,符合了这一前提,才可能成立。因此,被告人如地方法院所认定的那样,符合刑法第34条规定的可避免的禁止错误,不构成阻却责任的紧急避险。 (二)被告人P: 地方法院也正确地判决被告人P成立正犯。他和被告人H(其没有提出对刑事责任判决的上诉)一起, 通过他人实施了符合刑法第25条第1款的意义的犯罪。他们的行为出于卑劣的动机。因此两人都不只是教唆犯,因为共同被告人R也被定罪为正犯。 a)问题是,幕后者作为有责的行为之正犯是否可以是间接正犯,这是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最高法院尚未作出判决。联邦最高法院在其判决(德国最高法院刑事判例汇编BGHSt 2, 169, 170; 德国最高法院刑事判例汇编30,363, 364)中解释道,间接正犯是指没有亲自实施,而是通过他人实施犯罪行为的人。这一概念可以概括通常意义中的间接正犯,但是能否适用于本案有争议。在本案中,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因为被告人H和 P——根据地方法院所认定的——二人不符合谋杀罪未遂的教唆犯所要求的“阴险(Heimtücke)”这一犯罪构成要件特征。(相关见: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在 Dallinger MDR1969, 193; BGH, 06. Juli 1982 - 1 StR 281/82; Jähnke ,莱比锡法律评论,第10版,第 211章,编码 62, 64)。被告人P作为谋杀未遂的正犯受刑罚,因为她符合“其他卑劣动机(niedrige Beweggrunde)”这一构成要件特征。, 文献上关于教唆犯与间接正犯之界限问题存有争议 (相关见: Lackner, 刑法教科书,第17版,第 25章,编码1b)。按照大多数的观点,根据答责原则(Verantwortungsprinzip),当工具者自身是有责任的正犯时,不成立间接正犯(见:Jescheck, 刑法总论教科书,第3版,第540, 544页; Stratenwerth,刑法总论第一部,第3版,第 224页)。这同样也适用于本案中,犯罪工具者在一个可避免的错误中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况;不同于无责任能力(Schuldunfähigkeit)或者不可避免的禁止错误(unvermeidbare Verbotsirrtum)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中,犯罪行为人没有机会实施合规范的行为,在可避免的禁止认识错误中犯罪行为人享有实施合规范行为的机会。 Herzberg(赫兹伯格见其专著《正犯与共犯》,第22,23页)反对上述的观点。他认为,答责原则与将“可避免的禁止错误的行为人视之为犯罪工具者(Tatmittler)”的假设并不冲突;他作为故意的犯罪人的答责性的原因在于其过失地对禁止的无知;作为一个过失犯罪的“犯罪工具者”并不排除间接正犯的幕后者(mittelbare Täterschaft des Hintermannes)的情况。同样持这个观点的是Bloy(见其专著《刑法中以参与的形式作为归责类型》,第344,348页),他指出应当给予过失犯罪行为人与故意的犯罪行为人同样的判决——当故意犯罪是在可避免的禁止错误下实施时。Roxin(洛科信在Lange的论文集,第 173, 178 ff; 洛科信在莱比锡法律评论第10版,第 25章,编码 66 )认为,答责原则不能被运用于认识错误的案例中。他认为在犯罪工具者存在着可避免禁止错误的案件中,由于幕后者的多元决定性作用,间接正犯有存在的可能性。但是他具体区分了两类不同的案件(远远窄于Cramer 在Schönke/Schröder主编, StGB 第23版,第 25章,编码 38的看法):一类案件中,由于认识错误而没有认识到其行为的实质不法(而间接正犯有可能认识到);在另一类案件中(间接正犯没有可能认识到),清楚其行为的实质不法,却缺乏对形式违法性的认识(见Bloy 上书第 349及后)。 b)各种解决方案的侧重点各异,一种排他性地由依赖者对行为支配性决定,另一种则强调幕后者的决定性影响,这清楚地说明,该问题是一个开放性的评价问题(相关见:Maurach/Gössel/Zipf, 刑法总论第2部,第6版.第 220, 222, 237),没有明确的界定(相关观点见:Stratenwerth,上书,第 224页)。无论是从立法用语,还是间接正犯这一法律形象(Rechtsfigur)在直接正犯(unmittelbarer Täterschaft)与教唆犯(Anstiftung)构成的体系的地位中,都推导不出两种解决方案中任一种在原则上具有优越性。刑法第25条第1款所要求的无论如何不是如同从答责原则(Verantwortungsprinzip)中推导出来的那种,对间接正犯概念的狭隘理解。由于正犯形式的多样性,立法者意识到这一现实状态,而拒绝在立法中进行明确界定(相关见:Cramer 在 Schönke/ Schröder主编,上书中第 25章,编码 6; BT Drucks. IV/650 第 149页; V/4095 第 12页)。单独依靠答责原则的帮助,不可能得出一个清楚的界限,甚至连该理论的代表人物自己都承认,在通过一种权力机构而组织的犯罪(Machtapparat organisierten Verbrechen)案件中,不必考虑行为人在法律上完全的可答责性而承认存在一种“正犯后的正犯(Täterschaft hinter dem Täter)”(相关见:Stratenwerth 上书,第226页; Bockelmann/Volk, 刑法总论,第4版,第 182页)。不可避免的禁止错误(在这里间接正犯无疑是可能的)与可避免的禁止错误在评价上的比较表明,错误的可避免性本身不是合适的区分标准(Abgrenzungskriterium)。基于这样的认识错误而行为的人在行为时也缺乏对不法的洞察(Unrechtseinsicht)。他在具体场合所没有意识到其本来应当认识到的知识,但是这没有影响到许可行为发生的幕后者对犯罪行为的支配;至少幕前者可以被视为一个必要的犯罪行为的实施方式。在可避免的禁止错误的幕前者作为直接行为人的案件中,应当检验的是,根据承载着犯罪意志的客观性犯罪事实支配(objektive Tatherrschaft)为标准来判断幕后者是否为间接正犯(相关见: Maurach/Gössel/Zipf,上书,第 225页)。具体需要在具体案件中进行分析。这样的界定也符合于判断直接正犯与共犯而设定的基本原则。 区分的标准在具体情况下取决于错误的方式与范围,以及幕后者影响的强度(相似判决参见德国最高法院刑事判例汇编BGHSt 32, 38, 42)。杀人或者杀人未遂的间接正犯是指,在由其有意识地引起的错误的帮助下,事件如其希望发生,并且控制了事件的人。产生认识错误者在价值评判中被视为工具的人——虽然其行为(还)是有责的行为。 c)据查证,本案为:一方面被告人H和P引发了被告人R的幻想,后来为了打消R的法律上的疑虑和良心上的折磨,以及为了R能够按照他们的方案和计划去实施其希望发生的犯罪行为,其后又有意识地利用了R的幻想。通过这种心理上的方式,他们控制着整个犯罪计划。并且二人还确保了重要部分犯罪的实施。P给了被告人R实施犯罪的武器,并向他解释了如何实施犯罪的计划,比如他应当从后面行刺被害人,正如日本人和海军陆战队在二战中所作的那样,被害人可以立即毙命;周围不应当有目击者出现。R都遵照了这些特别的指示。另一方面,R在犯罪时不只是对其行为的禁止性产生了错误,毋宁说他更多地认为自己的控制力上受到了显著的限制。他认为自己处于一个紧密的关系和互相影响的网络中,被告人H和P利用了该网控制了他,以至于其很难从二人的特定影响中脱身出来。 因此被告人H和P决定着R对犯罪的实施,并通过其影响和优势的知识而操纵了犯罪行为的实施。他们因为对犯罪的控制作用,不是帮助犯,因为他们明知且愿意R独自实现客观的犯罪构成要件,同时不希望R的犯罪行为会被归责到自己的身上。 (三)上面的刑法判决不成立。 对所有被告人也不能适用刑法23条第 2款和刑法第 49条第 1款中关于减轻刑罚(Strafrahmenmilderung)的规定。即在这里这种刑罚的变动(Strafrahmenverschiebung) 应当被拒绝适用。这以犯罪行为人的实施行为的具体状态和人格作整体考察为基础。本案中,占有重要的意义的是,重要的与未遂相关联的犯罪具体要件——其行为接近于犯罪的完全实施,未遂行为具有的危险性以及犯罪能量的耗费(见BGHR刑法典第 23章,第2款刑罚的变动StrafrahmenverschiebungI, 2 和4)。刑事法庭尽管采纳了的这种观点。但是令人担心的是,它并没有权衡考虑到所有重要的有利于被告人的理由。判决理由表明,刑事法庭整体性的考虑了是否对被告人H和P适用刑罚的变动可能性,并没有对两个被告人进行区别论证。因此,在判决中不可能根据两名被告人对犯罪行为的贡献,判处不同的刑罚。她们共同地实施的犯罪行为,两人都是正犯。但是H是最重要的犯罪行为驱动力量;P管理了犯罪行为的实施,当然也是出于自己的利益。值得考虑的还有,地方法官根据刑法23条第2款,在检验的刑法减轻事由的框架内,对被告人H和P的人格变态行为(Persönlichkeitsabnormitäten)以及她们独特的关系网没有给与足够的衡量。H可以被视为是精神错乱的人格(gestörte Persönlichkeit)。 P是“三个被告人中最聪明的”;“但是却在哪儿都找不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稳定和可靠的价值的生活空间”。两个被告人在人格上的缺陷虽然不能导致适用刑法第21条,但是应当被考虑于刑法量刑中。但是这种可能性的实现被刑事法庭所阻隔,通过其未在根据刑法第23条第2款检验刑罚的变动时,同时考虑被告人的人格结构。 在原判决中对两个被告人的犯罪人格方面没有进行充分的评价。刑事法庭基于对被告人有利的相关犯罪情节的考量,适用刑罚的变动,不能再以刑法第211条谋杀罪判处二人终身监禁的刑罚。地方法院的这一考虑上的缺陷导致了两被告没有被适用终身监禁刑。同时也应考虑对被告人R废除适用有限的生命刑法,因为需要考虑的是,地方法院没有充分权衡他的人格结构,并可能因根据刑法23条第2款而适用的刑罚的变动;也就是,在该案中,禁止错误的不寻常的发生条件,以及被告人的控制能力受到明显的限制,这些都需要被同时考虑到。 因此刑事审判委员会认为,如果地方法院无法律错误的运用了刑法第23条第2款,对所有的被告人适用了一个轻缓的刑罚结构,那么该判决应该是成立的(换而言之,地方法院的判决有错误。译者注)。 (四)对地方法院判决的废止不涉及其对被告人R根据刑法第63条处置的无法律错误(rechtsfehlerfreie)问题。 四 争议与发展 猫王案是德国刑法正犯与共犯一章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案例,其中涉及该章多个重要的理论点,被众多教科书和学者作为重要的基本案例进行介绍。德国学者对该案基本上赞同最高法院的观点,下面以Gropp的观点为代表进行介绍。 他认为,在猫王案中,R以亲手犯的形式实施了杀害N女士未遂的行为。H与P可以作为与R有关联的间接正犯,当她们通过R实施犯罪行为,把R作为她们的犯罪工具。另外H和P可以因为两者的共同作用,作为共同正犯实施犯罪行为。那么H和P将是间接的共同正犯(mittelbare Mittäter)。在该案中,争议的关键是,H和P是否可能不是作为通过R未遂杀害N女士的间接正犯,而是仅作为R实施犯罪行为的教唆犯。R在他的幻想中,没有出于私心的动机(selbstsüchtige Motiven),而是为了拯救人类,才欲置N于死地。对于H和P而言,则自始至终存在着个人的动机:仇恨和嫉妒。另外H和P通过猫王的故事将易受影响的R控制于股掌之间。因此罪恶的一方应该是H和P。这种角色的分工也应当在刑法的参与体系(Beteiligungssystem)中得到体现。根据客观正犯理论中(objektive Täterschaftstheorie)的实质客观理论(die materiell-objektive Theorie),其主张可以将没有亲自实施犯罪行为的正犯,纳入间接正犯考虑,因此在该案中,可能将H和P视为间接正犯。根据严格的“以谁具有实施犯罪的意愿为标准来判断正犯 (die animus auctoris) ”的主观正犯理论(subjektive Täterschaftstheorie ),H和P由于具有明显的出于仇恨和嫉妒杀死N的犯罪故意而应当被视为正犯。而轻易受到影响的被告人R是帮助犯(Gehilfenschaft)。根据犯罪事实支配理论(Tatherrschafts-lehre)该案是在H和P的支配控制下进行的。值得考虑的是,R尽管他相信猫王的瞎话,而执行了杀害N的行为,这种行为是在“一种故意杀人的故意支配下进行的”。因此,是否应当考虑三人都是正犯。尽管在该案中,R基于认识错误,认为猫王的存在,并要求一个人类作祭品。但是R在犯罪行为的当时,很清楚地知道他将要杀死一个人,并且也希望杀死这个人。因此R是杀人未遂的正犯。最高法院认定了被告人H和P是间接正犯。因为尽管R作为工具,他意识到要杀人并对杀人的禁止具有理解和认识能力,H和P对整个犯罪行为有支配力。她们造成了R的幻想,并利用了R的幻想,运用心理控制方式控制了整个犯罪行为计划。同时她们也肯定了犯罪事实的重要部分。该案中,作为间接正犯的H和P的刑事可罚性开始的阶段是当R开始用匕首刺向V之时。R的刑事可罚性开始于其接近N女士之时。值得注意的是,应当区分H和P在该案中的作用,P是受制约于H的。 洛科信(Roxin)对该案也进行了评价 。他认为,最高法院的判决指出,幕后者具有对犯罪行为的支配,尽管犯罪工具者因为可避免的禁止错误而被视为故意的正犯。这不是意味着逻辑上有冲突。因为犯罪行为的支配有着不同的形式。直接正犯对行为有支配,其亲自支配着犯罪构成要件的实现,而间接正犯对犯罪行为有意志上的支配,其通过优势意志(强制或者欺骗等方式),支配着直接行为人,间接控制的犯罪行为的实施。在猫王案中,幕后者对犯罪行为实施人的支配建立在欺骗之上:她们欺骗R,让其认为是奉神的旨意行动。他将拯救数以百万计的人,从而排除了本可以阻止R杀人的障碍,R因此成了听从两位幕后者支配的工具。
- 上一条: 卢家仪 | 日本札幌法院:自杀游戏的罪与罚 2022-11-13
- 下一条: 张明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向他人提供电话号码,但没有其他信息,构成本罪吗? 2022-11-14
- 一份德国联邦法院关于柏林墙守卫的真实判决 2018-01-12
-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2022年最新判决:杀人与帮助自杀的界限 2022-11-13
- 德国版自杀游戏:联邦最高法院“垃圾袋致死案”裁判 | 2020-08-14
- 谭淦:从柏林墙射杀案看德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2021-10-12
- 德国版自杀游戏:联邦最高法院“垃圾袋致死案”裁判 | 李佳馨(译) 2022-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