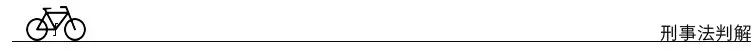德国联邦最高法院2022年最新判决:杀人与帮助自杀的界限
《刑事法判解》由北京大学法学院主办,陈兴良教授任主编,车浩教授任执行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发行。刊物关注刑事司法领域的实务问题,诚邀学界和实务界同仁赐稿。
公号&刊物来稿请至:xingshifapanjie@126.com

受嘱托杀人与帮助自杀的区分标准,是中外刑法教义学中历来的难题。与我国的刑法规定不同,德国《刑法典》第216条第1款明确将受嘱托杀人规定为刑事犯罪,而帮助自杀则基于共犯从属性的立场,被视为是不可罚的。这就导致对受嘱托杀人与帮助自杀的区分显得尤为重要。 对此,理论上通常采取的是所谓的支配标准,但在具体个案中,如何判断究竟是行为人还是被害人具有“支配”,则始终存在着困难性。尤其是考虑到,德国判例在正犯理论中过去往往采取所谓的“主观”标准,而在受嘱托杀人的场合,行为人恰恰是听命于被害人行事,此时,行为人在主观上仅具有“参与”的意志,这便可能导致受嘱托杀人罪在事实上的落空。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大量判例,不断填充“支配”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所谓的不可逆的“最后时点”学说。 下文介绍的这则案例,由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第六刑事审判庭于2022年6月28日作出(BGH , Beschl. v. 28.6.2022 − 6 StR 68/21)。这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截至目前,在这一问题上作出的最新判决。该判决作出以后,引发了不少德国学者的关注与讨论,在学界被认为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判例。其重要性体现在,它不仅进一步发展了“最后时点”的判断标准,同时也明确传达出德国司法实践对于生命自主决定权的高度保护。“刑事法判解”公号对该案的案件事实、裁判理由作了摘选与简评,供读者参考。 2019年8月7日,身患重病的E决定寻死。他用颤抖的手在笔记本上写下“我不想活了”,并且禁止他的妻子也即被告去请医生,他希望他剩下的药足以将他从巨大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在夜晚11点左右,他服下了家里所有的药片。被告过去曾是一名护士。被告在E的要求下,为E注射了六剂胰岛素。E因为身体虚弱,无法自己为自己注射。E甚至还直接向被告确认,被告是否已经为他注射了全部胰岛素,因为他不想行尸走肉般苟活。在次日凌晨3点半左右,E由于注射了过量胰岛素,因血糖过低而死。事后查明,E先前服下的各种药片事实上同样足以导致他的死亡,然而死亡时间会稍微推迟。 地方法院判决被告构成受嘱托杀人罪(德国《刑法典》第216条第1款),判处其一年有期徒刑(缓刑)。其主要理由在于,被告以积极的举动为E注射了胰岛素。尽管E对此具有明确认知,但在死亡来临的时刻,E并没有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被告为E注射胰岛素时,E已经决意接受他的死亡命运。但由于E并不知道胰岛素是否、何时会引发他的死亡,以及他至迟到哪个时点还有可能终结他的死亡命运,而被告恰恰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因此,E将他的生命交到了被告手中。换句话说,被告直至E死亡的“最后时点”来临之时,都在事实上支配着E的死亡进程。 联邦最高法院第六刑事审判庭驳回了地方法院的裁判,宣告被告无罪。被告的行为不构成杀人,而是不可罚的自杀帮助。其裁判理由摘录节译如下: 1. 受嘱托杀人与帮助自杀的界限 受嘱托杀人的行为人在事实上掌控了导致死亡的事件流程,即便他仅仅是在执行他人的自杀意愿。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谁亲手实施了终结生命的举动。如果根据整体计划,自杀者将自己交到了他人手中、接受此人夺走他的生命,那么这个人就构成了对事件的支配。相反,如果具有死亡意愿的人直到最后一刻,都保留着对他的命运的自由决定,那么,即便在此过程中他借助了他人的帮助,他的行为仍旧属于自杀。这不仅适用于因果流程由他本人开启的情形,且同样适用于因果流程由他人引起的场合。只要在行为人实施其行为贡献之后,求死者仍旧完全具备消除或终结其影响的自由,那么行为人就仅成立自杀帮助。 2. 在具体个案中对支配的认定 本案中,掌控死亡流程的并非被告,而是死者。这一结论并不会因为被告通过积极作为、给死者注射了致命的胰岛素而发生改变。如果仅仅孤立地对这一行为进行评价,那么就没能充分考虑以导致死亡为目的的整体计划。根据这一计划,E首先打算通过服用家中所有的止痛药、安眠药、镇静剂来终结生命,而注射胰岛素只是为了确保他最终寻死成功;因为他不想变成行尸走肉。在评价的视角下,服药和注射胰岛素在整体计划下是一个统一的终结生命的举动,其实施由E单独决定……根据这一整体计划,“是胰岛素导致了E的死亡,而药物原本要在更晚一点才会发生致命效果”这一事实,仅仅是一种偶然。考虑到这一点,地方法院的见解——即E将自己的生命交到了被告手中并让被告夺走他的生命——实际上并未充分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性。尤其是考虑到,在被告为死者注射胰岛素、完成了其积极的行为贡献之后,E仍旧掌控着导向死亡的事件流程。在此之后,他依然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清醒,并且自我负责地拒绝采取任何反对措施,例如要求被告请求救援等。 3. 本案不成立不作为的受嘱托杀人 被告的行为也不构成不作为的受嘱托杀人。尽管根据《民法典》第1353条第1款第2句,被告对其丈夫的生命和身体具有保证人地位……但是,从这一保证人地位中并不能产生针对本案这一具体事件的回避死亡的义务。因为她的丈夫的死亡意愿是在不存在任何认知与责任缺陷的情况下,自由地作出并对外表达的,这体现在他禁止她去找医生这一点上。这一死亡意愿构成了一种与情境相关的、对配偶生命的保护义务的免除。这同样适用于从医患关系或居住、生活共同体中产生的保证人义务……对于基于婚姻关系产生的保证人义务,这一点也没什么不同,尤其是考虑到,伴随着宪法法院关于自我决定死亡权利的判决,联邦最高法院第五刑事审判庭过去提出的、为了限定医生对病人生命的保护义务的理由,如今已获得了额外的重要性。这一权利同样适用于第三人,也即,当基本权利的行使依赖于第三人时,该项权利也保护第三人不受禁止……因此,当配偶基于一个自我负责的自杀决定陷入沉睡之后,救援配偶的刑法义务也不复存在……并且,被告将药拿给E、并为E注射了胰岛素,也不足以建立一种来自于先行行为的保证人地位。寻死者自我负责的决定——也即服药且不阻断注射胰岛素所开启的因果流程——已经否定了这一点。通过被告的前行为所提升的危险的实现,其风险完全处于E的责任范围之内。 4. 对第216条第1款的合宪性解释 联邦宪法法院针对《刑法典》第217条第1款(业务性促进自杀罪,已被宣布违宪)发展出的原则同样应当适用于第216条第1款,因为这一条文以类似的方式干涉了自我决定死亡的基本权利……法院认为应当对第216条第1款作合宪性解释。据此,如果具有寻死想法的人在事实上无法亲自实现他在不存在意思瑕疵情况下作出的自杀决定,而只能依赖其他人来实施能够直接导致死亡的行为,这种情形无论如何都应当被排除出该规定的适用范围。 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上述判决中,可归纳出如下裁判要旨: 1. 受嘱托杀人和不可罚的自杀帮助的界分,应当建立在对整个事件进行规范评价的基础上。 2. 如果死亡意愿是在不存在认识和责任缺陷的情况下作出并对外表示的,那么这将构成一种与情境相关的、对配偶生命的保护义务的免除。 帮助自杀和得同意杀人的区分,是一个经典的教义学难题。本案的核心争议点也在于,被告为打算寻死的丈夫注射胰岛素的行为,究竟构成受嘱托杀人,抑或仅构成对自我负责的自杀的不可罚的帮助。 在这一点上,主流观点采取了所谓的“最后时刻”标准,即考察在死亡结果不可逆转的最后时点,是行为人还是被害人支配着直接终结生命的举动。 但是,在一些具体情形下,究竟是谁支配着导致死亡的进程,并不容易判断。本案中的情形便是如此。一方面,行为人通过注射胰岛素,开启了导向死亡的因果流程,但另一方面,被害人E直到死亡来临之前,都随时有可能通过有效的手段回避死亡的发生。 对此,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一贯的观点认为,当求死者对于其死亡进程仍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但却有意识地不对其施加影响时,他就支配着不可逆转的时点。这一观点建立在Roxin学说的基础上。 文献上对此亦存在不少反对的意见,认为这样一种判断标准过度限缩了第216条的适用范围。这种反对意见进而主张,只要行为人事实上掌控着最后一个导致死亡的举动,那么他就构成杀人而非自杀帮助。 而在本案的裁判理由中,联邦最高法院则进一步延续、发展了其一贯的立场,并在此基础上更加明确地指出:可罚的受托杀人和不可罚的自杀帮助之间的界限,不能建立在自然主义视角的基础上,而应来自于对整个事件的规范评价。 当然,正如一些学者在批评意见中所指出的那样,什么是“对整个事件的规范评价”,在具体个案中仍旧是不清楚的,也即联邦最高法院新近提出的这一标准,并没能真正使受托杀人与自杀帮助之间的区分变得更加容易,不仅如此,这甚至可能导致“支配”和“正犯”的概念进一步相对化。 另一方面,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附带意见”中,法院基于保障生命自主权的根本立场,认为应当对第216条受嘱托杀人罪的适用范围进行合宪性解释,也即,对本罪的适用应以不妨害求死者自杀意愿的实现为限。换言之,如果过度扩张第216条第1款的适用范围,就相当于剥夺了具有自我决定权的、自我负责的公民,在自己无法亲手终结自己生命的情况下,假他人之手处分个人生命的权利。这构成了对基本权利的一种事实上的限制。不过,这样一种解释方向在立法和实践中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则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编译/ 陈尔彦
- 上一条: 非法拘禁罪结果加重犯的认定规则 ——以介入被害人因素为切入 2022-11-12
- 下一条: 德国版自杀游戏:联邦最高法院“垃圾袋致死案”裁判 | 李佳馨(译) 2022-11-13
- 德国版自杀游戏:联邦最高法院“垃圾袋致死案”裁判 | 2020-08-14
- 申柳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猫王案”的判决译介 2022-11-13
- 一份德国联邦法院关于柏林墙守卫的真实判决 2018-01-12
- 德国2022年最新裁判:防卫必要性的认定 2023-02-05
- 德国2022年最新裁判:防卫必要性的认定 2023-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