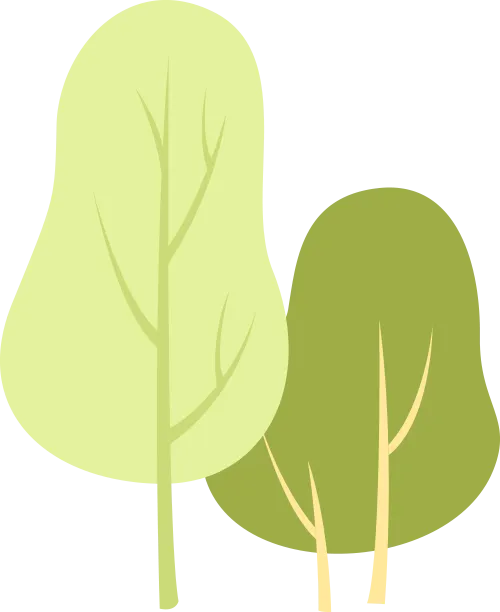张明楷:具体犯罪保护法益的确定方法
作者&文章简介 作者:张明楷,清华大学谭兆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具体犯罪保护法益的确定方法》,载《现代法学》2024年第1期。

2 摘要 SPRING 2024 在基本犯与加重犯的保护法益不同的情形下,应当分别确定基本犯与加重犯的保护法益。 如果拟制罪名与基本罪名的构成要件不同,就不应按罪名确定保护法益,而应分别确定拟制罪名与基本罪名的保护法益。 阻挡层法益与背后层法益是就不同犯罪或者基本犯与加重犯的关系而言,并不是任何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都包含阻挡层法益与背后层法益。 应当根据法益主体与被害人同意或承诺的有效性等要素区分个人法益与公共法益,不应当在对个人法益的犯罪中随意添加公共法益内容,也不宜随意在对公共法益的犯罪中任意添加个人法益内容。 此外,需要区分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与阻却违法性的优越利益,不应将阻却违法性的优越利益当作相关犯罪的保护法益。 3 文章结构 SPRING 2024 一、区分基本犯与加重犯的保护法益 二、区分基本罪名与拟制罪名的保护法益 三、区分阻挡层与背后层的保护法益 四、区分个人法益与公共法益 五、区分犯罪的保护法益与阻却违法的优越利益 4 文章梳理 SPRING 2024 小tips: 1、「对应梳理的“二”中的“其次”查看」 第二百九十二条 【聚众斗殴罪】聚众斗殴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多次聚众斗殴的; (二)聚众斗殴人数多,规模大,社会影响恶劣的; (三)在公共场所或者交通要道聚众斗殴,造成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 (四)持械聚众斗殴的。 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2、「对应梳理的“二”中的“最后”查看」 第三百八十八条 【斡旋型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写作方式归纳:(1)从具体罪名法条规定的现象总结规律,再提出问题。(2)收集具体罪名讨论文章中自己不认可的观点,并总结出共同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与应对。 本文主要讨论问题:不同学者对于同一犯罪的保护法益认定不同,既可能是由于刑法理论对具体犯罪保护法益的确定标准与确定依据缺乏相对一致的认识,也可能是因为对确定具体犯罪保护法益的基本方法存在分歧。本文就具体犯罪保护法益的确定方法发表浅见。 一、区分基本犯与加重犯的保护法益 只有确定了基本犯的保护法益,才能指导基本犯构成要件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加重构成要件。 加重犯的保护法益是否与基本犯的保护法益相同,取决于分则规定的加重内容或根据。如下: 第一种情形是加重犯只是不法程度的增加(不法的量的增加),故加重犯与基本犯的保护法益相同(加重的量刑规则)。 第二种情形是从立法论上说,有些犯罪应当以行为侵犯了另一法益为根据提升法定刑,但刑法分则并没有描述侵犯另一法益的行为,只是表述为情节严重或者情节特别严重,但在司法实践中,情节严重或者情节特别严重的内容包含了对另一法益的侵害。两种类型:一是不能事前确定 A 罪的加重犯会造成哪些法益侵害,故难以表述加重犯的保护法益,即使表述出来,也不具有特定性,没有实际意义。(例如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实施罪)二是A 罪基本犯的构成要件暗示了其加重犯会侵犯 B 法益,故能够确定 A 罪的加重犯会造成 B 法益侵害,因而能够表述加重犯的保护法益。在这种情形下,是分别确定基本犯与加重犯的保护法益,还是在确定基本犯的保护法益时就应包含加重犯的保护法益内容,是需要研究的问题。(例如抢夺罪的司法解释中其他严重情节包导致他人重伤的情况,因此抢夺罪加重犯保护法益包括财产与他人的生命、身体安全。)——张老师认为,对此在确定抢夺罪基本犯的法益时,就应将财产与生命、身体安全包含在内。 第三种情形是加重犯的根据并不是不法的量的增加,而是行为侵犯了其他法益。 在这种情形下,加重犯的保护法益显然多于基本犯的保护法益。 因此,不能按罪名确定法益,而应分别确定基本犯与加重犯的保护法益。但是,在确定基本犯的保护法益时,不能将加重犯的保护法益归入基本犯的保护法益。 否则,不利于对基本构成要件的解释。 二、区分基本罪名与拟制罪名的保护法益 从保护法益的角度来说,拟制罪名与基本罪名的法益保护既可能相同,也可能不相同或有所不同。后者主要是刑法是以整体不法程度相当为依据,或者为了定罪量刑的便利而作出了拟制规定。 首先,奸淫幼女型强奸罪与强奸罪的保护法益是否完全相同?本文看来,一方面肯定幼女享有性行为自主权,另一方面又不允许或者不同意幼女行使性行为自主权,有自相矛盾之嫌。因此,认为奸淫幼女罪的保护法益,是幼女的性的不可侵犯权或者性的完整无损性。 其次,刑法关于聚众斗殴罪的规定中存在法律拟制,如何表述聚众斗殴罪的保护法益?本文认为,以聚众斗殴行为可能致人轻伤为根据将人身权利作为保护法益存在疑问,即使致人重伤因为拟制故意伤害罪,因此人身权利不是聚众斗殴罪的保护法益。不能因为司法实践中将毁坏财产的结果作为聚众斗殴罪的从重情节,就将财产安全也作为聚众斗殴罪的保护法益。因此,只能将公共场所秩序作为聚众斗殴罪的保护法益。 最后,斡旋受贿不是独立罪名,如何确定受贿罪与斡旋受贿犯罪的保护法益? 普通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 只要行为侵害了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即使没有侵害职务行为的公正性,也完全可能成立普通受贿罪。 当然,加重的普通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则可能包括职务行为的公正性。 斡旋受贿犯罪的保护法益是被斡旋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以及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的不可收买性。 三、区分阻挡层与背后层的保护法益 在刑法分则中大量存在为了保护 A 法益(背后层)而保护 B 法益(阻挡层)的立法现象。(例如为了保护弱者的生命、身体设立遗弃罪,为了保护住宅内部的各种利益,先设立非法侵入住宅罪) 对于具体犯罪保护法益的确定,当然要考虑上述阻挡层法益与背后层法益的关系,但也不能一概认为,越是揭示出背后层法益,就越表明解释者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 质言之,除了真正的复合法益(复杂客体)外,对具体犯罪只需要表述出一个揭示犯罪本质、能够指导构成要件解释的法益;如果阻挡层法益是值得刑法保护的法益,背后层法益并不能也不应当对构成要件的解释起指导作用,就不应表述出背后层法益。 第一,阻挡层法益与背后层法益一般是就两个犯罪保护法益的关系而言的,而不是意味着要对任何一个犯罪都必须描述出阻挡层法益与背后层法益。(不同具体犯罪保护法益之间的关系,不是复合法益问题) 第二,如果阻挡层的保护法益是值得刑法保护的,就只需要将阻挡层的保护法益确定为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既不需要借助背后层法益来说明,也不应将背后层的保护法益作为该罪的保护法益。 第三,在确定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时,不能因为阻挡层的保护法益在前,背后层的保护法益隐藏在内,就只承认背后层的保护法益。首先,难以认为阻挡层的保护法益一概没有背后层的保护法益重要;其次,如果无穷无尽地追问为什么要保护此法益,就不可能形成对构成要件具有指导意义的保护法益;再次,如果对所有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都追溯到最终层面,那么,所有犯罪的保护法益都是一样的,因为国家法益与社会法益都应当分解为或还原为个人法益,于是,所有犯罪的保护法益都是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与人的全面发展;最后,如果对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都追溯到背后层的法益,则绝大部分犯罪都将成为抽象的危险犯。 四、区分个人法益与公共法益 由于各种原因,刑法理论比较习惯于对侵犯个人法益的犯罪添加公共法益内容,或者对侵犯公共法益的犯罪添加个人法益内容,导致侵犯单一法益的犯罪越来越少,侵犯复合(多元化)法益的犯罪越来越多,容易不当缩小罪名成立范围。 第一,对于侵犯个人专属法益的犯罪,不得确定为侵犯公共法益的犯罪,也不应添加公共法益的内容。只要行为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侵犯了个人法益(不存在违法阻却事由),就没有例外地属于不法行为,根本不需要判断行为是否破坏了社会秩序。 如果另外加入社会秩序的考量,就必然不当缩小犯罪的成立范围。 第二,凡是被害人的同意或者承诺阻却构成要件符合性或者违法性的犯罪,都是侵犯个人法益的犯罪,不得确定为对公共法益的犯罪,也不应添加公共法益的内容。 第三,在法益主体是个人的情形下,即使同意或者承诺无效,但如果无效的原因是基于有限的家长主义或者其他原因,也应当将侵犯该法益的犯罪确定为对个人法益的犯罪,不应添加公共法益的内容。因为当自己决定权的行使是给法益主体自身造成重大侵害结果时,对这种自己决定权进行适当限制,实际上是自己决定权的内在要求。 第四,只有当行为仅侵犯了个人法益并不成立犯罪,同时侵犯了公共法益才构成犯罪时,该犯罪的保护法益才是包括了个人法益与公共法益的复合法益;反之亦然。如果一个行为侵犯了个人法益,就必然直接或者间接侵犯公共法益,而且如果没有侵犯个人法益就不可能成立犯罪,则应确定为对个人法益的犯罪,没有必要加入公共法益内容。 第五,不能因为某种行为对象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就将相关犯罪确定为对公共法益的犯罪。 五、区分犯罪的保护法益与阻却违法的优越利益 作为阻却违法的更为优越的利益与构成要件保护的法益不必然是同一法益。亦即,虽然 A 罪的保护法益为 A 法益,甲所实施的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侵犯了 A 法益,但如果该行为保护了更为优越的B 法益,则甲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不成立犯罪。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 B 法益也是 A 罪的保护法益。 在本文看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并不包括政府、企业等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合理利用与处分。同时,刑法规定的侵犯知识产权罪的保护法益是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及社会公众对知识产品的合理需要也不恰当。 5 文章节选 SPRING 2024 法益对构成要件的解释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对法益的理解不同,对构成要件的解释就不同。但是,我国刑法理论关于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存在许多争议,或者说,就同一具体犯罪而言,不同学者所表述的法益内容并不相同,甚至出现了对同一犯罪部分学者认为是对个人法益的犯罪,部分学者认为是对公共法益的犯罪的现象。之所以如此,既可能是由于刑法理论对具体犯罪保护法益的确定标准与确认依据缺乏相对一致的认识,也可能是因为对确定具体犯罪保护法益的基本方法存在分歧。不可否认的是,对具体犯罪保护法益的确定,并没有公认的统一方法,不同解释者完全可能采取不同的方法确定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同时,“方法”是一个外延极为宽泛的概念,本文只是从刑法学界对保护法益产生分歧的原因(仅就笔者有限的观察)出发,就具体犯罪保护法益的确定方法发表浅见。 第一种情形是加重犯只是不法程度的增加(不法的量的增加),故加重犯与基本犯的保护法益相同。严格地说,这种情形的加重犯的成立条件并不是加重构成要件,只是加重的量刑规则。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71条第1款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职务侵占数额巨大与特别巨大,也可谓职务侵占罪的加重犯,但法定刑的提升只是基于不法的量的增加,而不是因为行为另外侵犯了其他法益。在这种情形下,基本犯的保护法益与加重犯的保护法益完全相同,解释者是只按基本犯确定保护法益,还是同时考虑加重犯确定保护法益,不会得出不同结论;如果形成分歧,则是基于其他原因。 第二种情形是从立法论上说,有些犯罪应当以行为侵犯了另一法益为根据提升法定刑,但刑法分则并没有描述侵犯另一法益的行为,只是表述为情节严重或者情节特别严重,但在司法实践中,情节严重或者情节特别严重的内容包含了对另一法益的侵害。其中又包括两种类型:一是不能事前确定A罪的加重犯会造成哪些法益侵害,故难以表述加重犯的保护法益,即使表述出来,也不具有特定性,没有实际意义。例如,《刑法》第120条之四规定了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实施罪,其加重犯既可能侵害人身法益,也可能侵害财产法益,还可能侵害其他公共法益,不可能事前确定。对这类犯罪没有必要也难以事前确定加重犯的保护法益。二是A罪基本犯的构成要件暗示了其加重犯会侵犯B法益,故能够确定A罪的加重犯会造成B法益侵害,因而能够表述加重犯的保护法益。在这种情形下,是分别确定基本犯与加重犯的保护法益,还是在确定基本犯的保护法益时就应包含加重犯的保护法益内容,是需要研究的问题。例如,我国《刑法》第267条第1款规定:“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抢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从法条的表述来看,似乎应当认为加重犯只不过是不法的量的增加,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司法实践中不乏抢夺行为致人伤亡的案件。正因为如此,2013年1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25号)第3条与第4条规定:抢夺公私财物导致他人重伤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67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抢夺公私财物导致他人死亡的,应当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既然如此,就应当认为,抢夺罪的加重犯的保护法益包括财产与他人的生命、身体安全。 第三种情形是加重犯的根据并不是不法的量的增加,而是行为侵犯了其他法益。在这种情形下,加重犯的保护法益显然多于基本犯的保护法益。因此,不能按罪名确定法益,而应分别确定基本犯与加重犯的保护法益。例如,倘若说故意伤害罪的基本犯的保护法益是人的身体健康,那么,在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场合,其保护法益就不只是人的身体健康,还包括人的生命。换言之,既没有必要说故意伤害罪的基本犯的保护法益包括人的生命,也不能说故意伤害罪的加重犯的保护法益仍然只是人的身体健康。再如,强奸罪的基本犯的保护法益是妇女的性行为自主权,但强奸致人重伤、死亡的加重犯的保护法益,则除了性行为自主权之外,还包括妇女的身体健康与生命。 刑法理论关于某些犯罪的保护法益之所以存在不同表述与争议,一个重要原因是,就同一具体犯罪而言,有的学者仅表述了基本犯的保护法益,有的学者同时表述了加重犯的保护法益但又没有区分基本犯与加重犯的保护法益。例如,关于绑架罪的保护法益,一种观点指出:“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他人的人身自由权利、健康、生命权利以及公私财产所有权利……至于在复杂客体中,立法将本罪规定在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中,说明人身权利是客体的主要方面。”据此,绑架罪的保护法益首先是人身自由权利、健康、生命权利,其次是公私财产所有权利。但在本文看来,这种观点将绑架罪的基本犯的保护法益与加重犯的保护法益,乃至由绑架行为形成的牵连犯的保护法益,都纳入到绑架罪的保护法益,似有不妥。一方面,成立绑架罪并不以侵犯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为前提,否则,就意味着伤害行为、杀人行为成为绑架罪的构成要件要素,这明显缩小了绑架罪的处罚范围;另一方面,所谓对公私财产所有权利的侵犯,既不是成立绑架罪基本犯的条件,也不是成立绑架罪加重犯的成立条件,只是实现勒索财物目的时的一种情形,而此时所成立的敲诈勒索罪,只不过与绑架罪构成牵连关系,故公私财产权利并不是绑架罪的保护法益,而是相关的牵连犯的保护法益。正因为如此,上述观点不能不承认,“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虽然也是使用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将他人掳为人质,但并不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而绑架他人,所以只侵犯到他人的人身自由、健康、生命权利”。既然如此,充其量只能说,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罪是复杂客体,而不能认为所有类型的绑架罪都是复杂客体。 刑法分则规定了一些拟制罪名,其中有的是刑法分则条文明文规定的拟制罪名,有的是原本可以确定为独立的罪名,但司法解释仍然将其确定为拟制罪名。前者如《刑法》第269条规定的事后抢劫或准抢劫行为,由于法条明文规定“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而《刑法》第263条规定的是抢劫罪,故司法解释对《刑法》第269条规定的犯罪只能冠之以抢劫罪的罪名。后者如《刑法》第388条规定的斡旋受贿,尽管法条表述为“以受贿论处”,但其实可以将本条规定的犯罪概括为斡旋受贿罪,只不过司法解释仍然将本罪确定为受贿罪,导致斡旋受贿成为拟制罪名。 在本文看来,一方面肯定幼女享有性行为自主权,另一方面又不允许或者不同意幼女行使性行为自主权,有自相矛盾之嫌。事实上,幼女的性的自由原本就受到了严格限制,倘若只是由于幼女缺乏自己决定能力而阻却同意效力,似乎意味着可以由家长、监护人代行决定,但法律并不允许。应当认为,奸淫幼女罪的保护法益不同于普通强奸罪的保护法益。幼女由于身心发育不成熟,对性行为的意义缺乏理解与判断能力,因此,为了使幼女健康成长不受性行为的妨碍,必须一律禁止对幼女实施性交行为。在此意义上说,奸淫幼女罪的保护法益,是幼女的性的不可侵犯权或者性的完整无损性。 刑法为了周全地保护法益,尽可能不遗漏各种犯罪,不得不从不同侧面与角度规定各种犯罪。又由于法益的种类繁多,所以,刑法分则对法益的保护形成不同的构造。例如,数个法条既可能分别保护不同的法益,也可能共同保护相同的法益;数个法条保护的法益之间既可能缺乏密切关联,也可能具有密切关系,后者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形就是两个法益之间具有阻挡层与背后层的关系。换言之,在刑法分则中大量存在为了保护A法益(背后层)而保护B法益(阻挡层)的立法现象。 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是个人法益还是公共法益,通常是比较容易区分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刑法理论比较习惯于对侵犯个人法益的犯罪添加公共法益内容,或者对侵犯公共法益的犯罪添加个人法益内容,导致侵犯单一法益的犯罪越来越少,侵犯复合(多元化)法益的犯罪越来越多。例如,有观点认为,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的保护法益是“公民的通信自由权利和邮电部门正常的活动”;报复陷害罪的保护法益是“公民的控告权、申诉权、批评权、举报权等民主权利和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这显然是对侵犯个人法益的犯罪添加了公共法益的内容。再如,有观点指出:“招摇撞骗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国家机关的威信及其对社会的正常管理秩序,其次要客体是公共利益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这明显是对侵犯公共法益的犯罪添加了个人法益的内容。 第一,对于侵犯个人专属法益的犯罪,不得确定为侵犯公共法益的犯罪,也不应添加公共法益的内容。例如,不能认为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保护法益除了生命、身体健康之外,还包括社会秩序或者公民的安全感。再如,也不能认为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的保护法益除了公民的身体活动自由与住宅权或住宅安宁外,还包括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只要行为符合上述犯罪的构成要件,侵犯了个人法益(不存在违法阻却事由),就没有例外地属于不法行为,根本不需要判断行为是否破坏了社会秩序。如果另外加入社会秩序的考量,就必然不当缩小上述犯罪的成立范围。更为重要的是,对侵犯个人法益的犯罪添加公共秩序的内容,会导致将个人法益当作手段,使个人法益是否受侵犯成为社会秩序是否受侵犯的判断资料,从而仅将社会秩序的维护当作目的,这不符合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观念。 第二,凡是被害人的同意或者承诺阻却构成要件符合性或者违法性的犯罪,都是侵犯个人法益的犯罪,不得确定为对公共法益的犯罪,也不应添加公共法益的内容。被害人对自己享有处分权限的法益给予同意或者承诺时,该同意或承诺才是有效的。反过来说,同意或承诺有效,表明加害人的行为并不成立犯罪,表明被害人处分的是自己有权处分的法益,当然属于个人法益。所以,就侵犯个人法益的犯罪而言,在个人法益之外添加公共法益的内容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被害人同意或者承诺有效的场合,不可能因为行为侵犯了公共法益而成立犯罪,至于是否成立其他犯罪,则是另一回事。例如,在两名妇女同意与两名男性在公共场所性交的情形中,两名男性不可能成立强奸罪。至于四人是否成立聚众淫乱罪则是另一回事,但不能将聚众淫罪的保护法益纳入强奸罪保护法益的范围。可是,我国刑法理论常常对被害人的同意或者承诺阻却构成要件符合性或者违法性的犯罪添加公共法益内容。 第三,在法益主体是个人的情形下,即使同意或者承诺无效,但如果无效的原因是基于有限的家长主义或者其他原因,也应当将侵犯该法益的犯罪确定为对个人法益的犯罪,不应添加公共法益的内容。例如,对儿童的犯罪都是对个人法益的犯罪,而不管儿童的同意或者承诺是否有效或对量刑是否产生影响。应当认为,奸淫儿童、猥亵儿童、引诱幼女卖淫、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等,都是对个人法益的犯罪。 第四,只有当行为仅侵犯了个人法益并不成立犯罪,同时侵犯了公共法益才构成犯罪时,该犯罪的保护法益才是包括了个人法益与公共法益的复合法益;反之亦然。例如,《刑法》第300条第2款规定的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致人重伤、死亡罪,就包含了对公共法益与个人法益的侵犯,仅侵犯其中一项法益,就不可能成立该罪。如果一个行为侵犯了个人法益,就必然直接或者间接侵犯公共法益,而且如果没有侵犯个人法益就不可能成立犯罪,则应确定为对个人法益的犯罪,没有必要加入公共法益内容。这是因为,在这样的场合,刑法对公共法益的保护只不过是对前一法益的保护的反射效果或者附随效果,而且由于对个人法益的侵犯必然直接或间接侵犯公共法益,所以,公共法益是否受到侵犯是不需要判断的,也不需要以该公共法益为指导解释构成要件。例如,刑法将诬告陷害罪规定为对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事实上,任何符合诬告陷害罪构成要件的行为都必然妨害司法活动,尽管如此,也不应当将司法活动作为诬告陷害罪的保护法益。 第五,不能因为某种行为对象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就将相关犯罪确定为对公共法益的犯罪。有学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仅直接关系个人信息安全与生活安宁,而且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安全乃至于信息主权;所以‘公民’一词表明‘公民个人信息’不仅是一种个人法益,而且具有超个人法益属性,还需要从公民社会、国家的角度进行解释。”本文难以赞成这一观点。公民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都关系社会公共利益,但不可能认为这些法益是公共法益。再如,选举权与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密切相关,但不能认为破坏选举罪是对公共法益的犯罪。在判断一个犯罪的保护法益是个人法益还是公共法益时,不能仅以行为对象为依据,还必须以构成要件行为为依据。 刑法在决定是否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时,第一,“需要检讨设置刑罚法规处罚该行为,是不是为了达成规制目的的有效手段(手段的适正)”。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以一定的确实可靠的方法确认该行为的有害性”。第二,“需要检讨为了实现规制的目的,是否确实有必要采用刑罚这种(以侵害法益为内容的)严厉制裁?这种制裁是否属于对该行为的过度对应(侵害的必要性)?”第三,“在包括性地衡量设置刑罚法规所丧失的利益与所获得的利益时,所获得的利益是不是更大(利益衡量或狭义的比例性)?”就此而言,特别需要判断的是,刑罚的适用在对法益起保护作用的同时,会给全体国民的各种活动产生什么影响(附随的萎缩效果)。这种法益之间的对立与协调,既是刑事立法要考虑的,也是刑法解释要考虑的。
- 上一条: 张明楷:具体犯罪保护法益的确定依据 2024-09-14
- 下一条: 邓毅丞:财产性利益的刑法保护范围——以诈骗罪的认定为中心 2024-09-18
- 张明楷:具体犯罪保护法益的确定依据 2024-09-14
- 张明楷|具体犯罪保护法益的确定标准 2023-12-30
- 张明楷|具体犯罪保护法益的确定标准 2024-09-14
- 张明楷刑法学第五版 2016-11-14
- 张明楷:《诈骗犯罪论》前言 2021-05-19